从《西学东渐》到《师夷长技》 ——中国近现代科技转型学术研讨综述
日期:2020-05-07从《西学东渐》到《师夷长技》
——中国近现代科技转型学术研讨综述
王薇(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博士生)
刘大椿教授主持的《西学东渐》《师夷长技》两部著作,于2018年和2019年先后出版以来,引起了学界和广大读者的关注。与两部著作相关的几篇访谈及书摘文章,先后在腾讯与网易历史网上获得了超过5万的阅读量。2019年10月13日,人大出版社与单向街书店合作举行了“哲学咖啡馆”交流活动,以“从《西学东渐》到《师夷长技》——中国近现代科技转型的艰辛与启示”为主题,邀约六位国内著名学者对谈,除了现场的70余名观众外,活动由凤凰网现场直播吸引了3000多人在线观看,刘大椿教授携这两部书进入了大众的视线。随后,11月23日,受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之邀,刘大椿教授又赴国图古籍馆临琼楼,以“两波西学东渐的艰辛与启示”为主题,为现场两百多位读者带来了一场系统完整而又细节丰富的精彩讲座,成功拉近了学术与大众的距离。紧接着,11月30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围绕《西学东渐》、《师夷长技》两部书,举办了一次全国性的“西学东渐与中国近现代科技转型”学术研讨会,以图把相关研究深入下去和延申开来。此举得到学界的积极回应,有来自全国38所高校及科研院所的7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收录论文36篇,与会者涵盖了哲学、历史、宗教、文化等诸多领域。(参与单向街书店的“哲学咖啡馆”对谈的,有刘大椿教授、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刘益东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聂敏里教授,北京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中心主任张大庆教授,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杨舰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所所长刘孝廷教授等。)

《西学东渐》与《师夷长技》是以中国近现代科技转型为主题(内容跨度几近400年)的学术著作。刘大椿教授将转型分为两个阶段:《西学东渐》一书讲述了西学东渐第一波,即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至西学东源的阶段;《师夷长技》一书沿着主脉络记叙了西学东渐第二波,即晚清至民国的师夷长技的阶段。
两本书强调了三个重要的历史节点和四个形容转型特征的术语。1583年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入住中国为第一个节点,在此之前中西方科技在各自的轨道上并行发展,并无比较的公认标准,是在传教士的作用下,东西方科技才开始有了交集。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比较顺利,不论是士人还是君主都向新奇的西方科学技术开启了大门,这也使得中国在17世纪出现了科技转型的可能。然而到了作为第二个节点的1700年,亦即17、18世纪之交,曾经拥抱科学的康熙帝在晚年主要是为了维护大一统王朝的统治,开始积极实施文化专制与闭关锁国政策。不少饱学之士在康熙帝圣谕号召下对西方科技的态度从“西学东渐”转变为“西学东源”,为西方科技现象寻求中国解释源头的研究方式扼杀了科技转型的可能。直到19世纪,国人包括清政府经历了太平天国运动以及列强入侵的内外交困,方才明白只有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才能救中国。于是有了1860这个节点,此即第三个节点。由自强运动(同光新政)开启了“师夷长技”的自觉转型历程,历经曲折坎坷的百年践行后,中国终于基本完成了现代化的科技转型。刘大椿教授用四个术语——“平行发展”、“西学东渐”、“西学东源”与“师夷长技”,来总结这段跨越四百年的曲折坎坷却锲而不舍的科技转型史。
就前两次活动现场观众互动及网络传播反响的情况来看,读者在两本书的启发下,所关注的话题主要在于中国科学技术的古今对比、现代科技转型、中西科技文化的交流和冲突等方面。而研讨中学者们对于两书内容、问题及启示的关注则集中于以下四个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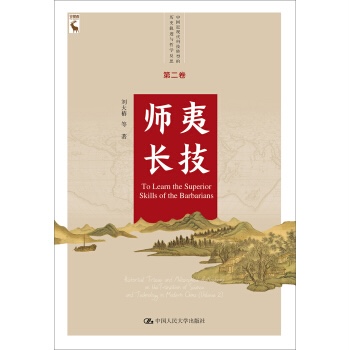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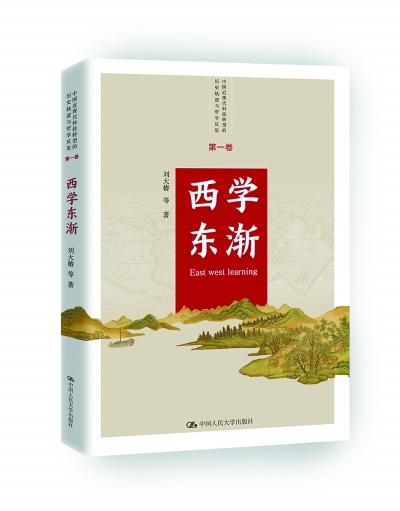
一、关于研究范式的创新和方法论的启示
正如刘大椿教授在书中所言:“西学东渐的故事很精彩,但要讲好这个故事却不容易。第一,需要花大力气钩沉史料,去伪存真;第二,需有大智慧谋篇布局,设计一个直达主题的结构。”两部书的叙事结构是以西学东渐的历史进程为暗线,采取总叙和分叙结合、特写和铺陈交叉的方式推进的。以《西学东渐》一书为例,刘大椿教授首先讲述16世纪末至17世纪西方科技东传的缘起和基本历程。其次,以利玛窦和徐光启为案例,特写了西学东渐如何发生和突破、中西科技之间的交集如何形成、科技东移如何取得成效。接着又有概述,介绍明末清初西学东渐如何通过皇帝、耶稣会士与士大夫之间的多方合作获得显著成效。另外还有浓墨专论康熙帝与西学,强调了酷爱科学的皇帝又是如何让西学东渐变成西学东源,结果导致西学的式微。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刘益东教授指出,通常科学史的研究被分为内史、外史、人物史等研究范式,以萨顿的科学编年史、柯瓦雷的科学思想史、默顿的科学社会史为代表。然而历史研究面临着如何整合碎片化史料的挑战,加之专门史需要专业背景知识,难以获得广泛的重视,故使科学史学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困境。面对碎片化问题,刘益东教授认为,刘大椿教授这两部书以整体史观统摄史料碎片、进行模块化梳理与整合的特点,为科学史研究提供了一种整体史研究的方法。首先,史学是以史料为基础的学问,而史料存在的形态是离散的、碎片化的,史学的基本任务是如何把史料碎片有机地组织、整合起来,以呈现出历史整体的形态与意义。两部书的谋篇布局体现了科学哲学思想对于历史碎片的一次成功整合,这种整合让历史碎片找到自己的位置,相互联系产生意义,从而聚合成结构性的模块,共同构成与整体的必要联系。其次,历史资源应当是最重要的资源之一,从科技转型的角度研究这段历史,加之寓思辨于故事中的写作风格,不仅可能扭转科学史边缘化的趋向,还可使很多未充分解读的史料得到更好的理解,因此可以说《西学东渐》和《师夷长技》,开启了资源史学的研究。
中国科学院大学韩琦教授指出全球史的视野是近50年来受追捧的研究方向,两部书从思想和技术的传播看欧洲和中国的科技发展,横向联系了各国的来往和互动,具有全球史观般宏观的视野和理论的高度。
北京师范大学刘孝廷教授评论两部著作有深广度、经纬度、汇集度和启示度,不仅体现在内容与形式的精心打造和勾勒上,还在某种程度上很大地改变了学界对这段历史的看法和研究走向。由哲学家来书写历史,能够由哲入史,由史入实,不仅让人反思历史中例如“给”与“取”、“科学”和“宗教”、“制度”和“文化”等概念,还体现了对现实的忧患意识。


二、对康熙帝与传教士关系的历史审视
《西学东渐》书中对“康熙帝与西学”的特写耐人寻味。刘大椿教授指出,康熙帝在位62年,是一位钟情科学的皇帝,康熙时代在科学上的成就足以彪炳史册,然而他与西学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前期与晚期也有很大区别。他虽然鼓励西学东移,也善于利用传教士和西学知识,然而在他的晚年,当满清帝国成功地回归为传统中国的大一统专制王朝之时,为巩固其统治,不仅实行禁教政策,并且对西方传教士传播进来的科学技术进行特殊阐释,得出“西学东源”的结论。西学在中土传播受阻,最终与同时期正进入“巨人时代”的西方科技发展分道扬镳,于是中国无奈地错过了一个近现代科技转型的机会。
学者们对这一史实进行了大量回应,韩琦教授的研究采取从全球科学文明史的视野,探讨康熙时代不同时期耶稣会士的作用,与欧洲科学机构的交往,及对科学传播的贡献。康熙时代是有清一代中外交流最为频繁的时期,荷兰、葡萄牙、俄国、罗马教廷曾派遣使节,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也派遣“国王数学家”来华。康熙帝为编纂历算著作,制造火器、玻璃和珐琅,聘用了许多传教士。殊不知此时的法国将输送传教士作为国家行为的一部分,外交、政治与宗教的传播融为一体。由于传教士力劝,康熙下令开启耗时费力的地质勘测,取得《皇舆全览图》这样的瞩目成就,而法国本土此时却无法举全国之力进行大规模的测绘,科学也成了康熙皇权的重要体现。上海交通大学学者安烁羽与董煜宇则指出,传教士带来的西方地理测绘知识提供了测绘活动的理论基础。康熙时期的地图测绘活动不仅促进了中西科学文化的交流、推动了中国测绘技术及制图学的发展,发现了地球扁圆说的事实证据,还加强了大一统国家的治理与疆界的稳固。
通过对《钦定格体全录》以及对巴托林(Thomas Bartolin)人体解剖学底本的研究,北京大学张大庆教授对于康熙与西学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解读。他认为康熙帝的科学观其实停留在将科学技术看作奇技淫巧的阶段,科学知识成为其炫耀皇权和个人能力的资本,而非一种新的规范。在这个层面上科学与权力是从属的关系。科学知识的接受、选择与传播过程中其实不仅仅是西方常用的“冲击-反应”理论,皇帝的角色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因而成为更为复杂的主动选择与被动选择的问题。
三、关于文化碰撞与科学传播的关系
中西文化的异质性众所周知,伴随西方传教士而来的科学技术,作为16、17世纪西学的代表,如何在明末清初的政治文化背景下得到广泛的传播,甚至深刻影响到中国科技的发展一直是受到关注的重要问题。对于中西文化与科技传统的讨论中,“李约瑟问题”成为较为有争议并广泛讨论的话题。作为该问题的回答,刘大椿教授认为,明代以前中西方科学技术乃是各有所长、平行发展,直到明代以后西方耶稣会传教士带来了西方的科技,由此中西方科技开始有了交集,尤其是在17世纪明末清初时期,两者的汇通达到非常可观的水平。然而18世纪的满清帝国在政治体制、思想观念等方面完全趋向于保守和自我封闭,自觉和不自觉地排斥西方科学技术。康乾盛世不但在文化上排斥西方天主教,而且在科学上贬低和排斥西方学术思想,甚至得出西学东源的结论。使得中国在第一波西学东渐中,失去了透过吸纳西方近现代科技来实现科技转型的机遇。(参见刘大椿,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与中国近现代科技转型,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8年第6期,153-154页。)两种文化碰撞的结果直接作用于科技文化的传播以及科技转型的结果,禁不住引人深思。
康乾盛世是西学东源思潮的沃土,乾隆年间兴起《四库全书》编纂的文化工程,同样也对西方科技的传播带来了冲击。中国政法大学学者郑云艳通过对乾隆年间所编纂《四库全书总目》中泰西人作品著录的考察,发现在《四库全书》编纂之时,西人身份著录有许多混乱之处,大量“西学”曾被打上“古学”的标签,反而成为了“中学”代言者,反映了当时中国流行的“西学中源说”。另外,18世纪的“西学”能够被认可的前提,亦需要以“古学”为依托。
针对这段历史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段伟文教授将清初的政治文化视作科技传播的壁垒。科技与政治、科技与文化之间有其特殊的关系,康熙帝正是强化了科技与政治间的“牢结”关系,所以导致了西学东源的结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周伟驰教授主要关注的是,晚清新教传教士的科技观与今天的通常观念之间的差别。人们一度认为科学与宗教是敌对的,但晚清之时来华的传教士多认为科技与基督教信仰并不矛盾,认为科技所揭示的世界正显示了上帝创造的美妙。这种基于千禧年主义影响下的“大觉醒运动”驱使新教传教士大规模进入中国,对世界上的“边远”地区进行教化。传教士认为要破除中国人的“迷信”,传播新教文明观最有力的武器还是现代科学知识。
中国社会科学院刘国鹏教授指出,晚明至晚清中华帝国面对西学冲击的认知和反馈机制应当基于全球化的事实、知识和心理来考量。此时虽然中国本土的精英阶层保持着和来华耶稣会士群体的密切交往,但由于中国抱持着差序格局的夷夏天下观,中国普遍欠缺全球化的视野,对西欧宗教改革与世界变化茫然无知。此时西欧文明正在由纯粹的基督教文明向日益世俗化,向日后无远弗界、影响全人类的现代文明快速转变,然而中华文明系统仍处于一种静态模式的自我复制,通过“西学东源”这一对待外来文明的自慰做法维持和强化天朝之居于全球文明链条顶端的封闭心理。这使得两种文明、两种价值的较量中,“天朝”文明无可争辩的被地方化。
中国农业大学李建军教授认为,不仅仅是新近出版的《西学东渐》和《师夷长技》,刘大椿教授1995年出版的《新学苦旅》实质上开创了一门可称为科学文化学的学问,从文化的和价值的视角探讨科技转型及其意义。我们今天思考科技转型问题,以及科技创新面临着的许多瓶颈问题,如果能从文化和价值层面去思考会有更多启示。
四、关于近现代科技转型的解释模式
自晚清至民国,内忧外患,形势艰危。国人之先进者,自觉技不如人,学习西方,实现中国科技和教育从传统到近现代的转型,成为目标明确、锲而不舍的追求——通过百年不间断的“师夷长技”才使得中国的科学和技术实现了近现代转型。转型中体现出一些重要、多样且复杂的特点,回望近400年的历史轨迹,能带来诸多的思考和展望。刘大椿教授希望对近现代中国科技转型中所出现问题的讨论,能够推进科学哲学、科技史以及诸多学科进一步的研究,并且对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的未来发展带来启示。许多学者对此给予积极回应。
中国人民大学聂敏里教授试图用两种富有启发性的社会变革模式,来审视和解释科技转型过程中由“西学东渐”到“西学东源”的历程。当17、18世纪西方传统转向加速增长的变革模式之时,中国仍处于前现代社会的周期变革模式。他指出整个四百年西学东渐过程期间种种反复与曲折的表现,正是两种社会变革模式在重叠与交织中所起到的根本制度性条件约束作用的结果。科学技术有为自身创新和发展提供可能空间的制度需求。透视中国现代化制度转型之艰难的更深层次的历史原因,是囿于科学技术所需的制度内涵和封建专制制度的水土不服。
回顾历史,段伟文教授注意到从西学东渐到师夷长技乃至整个中国现当代科技转型的过程中,以徐光启为代表的诸多“居间人”在联结中国与世界,以及科技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领域上发挥了关键作用,极大地玉成了科技转型过程中科技与各在地因素的相互接受。不仅师夷长技过程需要“居间人”从中作用,通过观察“居间人”角色的特性,更可探寻科技联结中国与世界、科技纵贯过往与未来等宏大的居间性运作的路径、习惯和盲点,进而为中国未来科技发展指出可能的方向,以规避一些固有的迷思。
关注于近现代科技转型中科学观念的更迭,刘孝廷教授指出国人的科学观经历了几重变迁:从科学服务于信仰的“传教士科学”、作为工程技术实用工具的技术化的“洋务科学”、变法时上升为意识形态的“唯科学主义”、作为民族解放力量的“救亡科学”乃至将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新洋务科学”,科技转型问题实质上仍然延续至今。但是出于各种原因,刘大椿教授的书中并未展开对该问题的讨论。基于科学特性和历史沿革的标准对应性,我们能够发现科学的精神性和功利性在不同历史时期或聚合或先后占据观念高点,但并没有恢复纯粹的科学观。回顾转型的历史应当让当下的人们重新思考科学的意识形态性和工具性之间的平衡,调和纯粹自由的科学维度与社会的科学维度之间的张力,亦或寻找第三种新的科学以适应当前历史发展的需求。
刘国鹏教授认为,尽管科技发展面对全球化的事实、知识和心理因素,我们今天仍然存在某些历史现象的重复,某些网红学者发表诸如“英语发源于中国”的研究实质上是当下一些学术研究中体现出来的“西学东源”借尸还魂的现象。与此同时,西方现代化潮流成为文化底色这一事实已成为中国人无法置身事外的真正挑战,不应当作历史公案一笑了之。
《西学东渐》与《师夷长技》是刘大椿教授二十多年持续研究的成果,刻画了中国近现代科技以及教育转型的历史轨迹,通过其整合式的研究方法,为读者展示了波澜壮阔的中国近现代科技转型史背后的细节和重要理念。这两部著作关于现当代科技转型的深刻思考,对未来科技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亦得到了来自学者与读者的深切共鸣和积极回应。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郝立新院长认为,这两部著作毫无疑问是科技哲学、科技发展史研究的一个精品。随着我国开放程度的加深,需要站在科技哲学与科技史的立场重新对历史碎片进行整合。叩问中国近现代科技转型的历史轨迹问题,即是对历史进行的批判重建。
从当前学者的研讨内容以及读者的反馈得以看出,二者关注的重点实际上是高度重合的。这两部著作提供了一个正视历史中所出现问题的机会,有助于对当下的科技发展以及教育领域的改革保持清醒的认识。期待这两部书的传播与研讨能够启发出更多的思考。
(原文发表于《自然辩证法研究》202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