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文 | 孔颜之乐的精神境界
日期:2023-11-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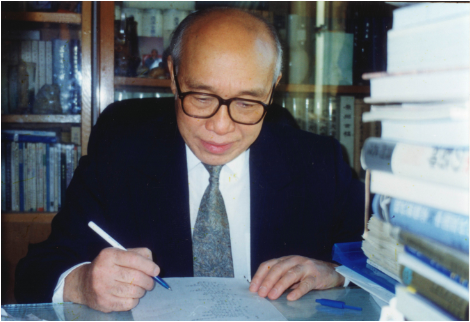
摘要:中华民族五千年光辉灿烂的文明,一直延续至今,在“协和万邦”价值观指导下,形成“共识中国”的理念,构建了礼乐文明,以更替巫术文化。自周公制礼作乐,渐成主导的文化意识,礼别乐和。其端始、构建,都是为化解人性中的邪念、淫思,行为中的贪暴、动乱;激发起人的善心,以至于真善美的境界,而导向孔颜之乐。人是有情的和合存在,这是人普遍具有的一种感受。中西情感有异,是为乐感情感与罪感情感。中国从人性善出发,乐于求道、问道、悟道于自然社会。人生实践,是多元、多样实践的体悟和感受,而激荡于乐感情感。由于人的无止境的求道,其理论思维具有开放性、多元性,因而构建乐山乐水,乐而忘忧的孔颜之乐的思想境界。
关键词:精神境界;孔颜之乐;礼别乐和;乐感罪感
三《易》(《连山》、《归藏》《周易》)开启了儒道墨三家思想,是中国哲学理论思维的源头活水。孔子读《周易》竟至“韦编三绝”,可见对《周易》作了尽精微的研究,所以后人把《易传》归于孔子名下。其“保合太和”“首出庶物,万国咸宁”是三家共同的愿望。至于如何实现天道合于人道、人们安居乐业、社会和谐发展的愿望,各派哲学有不同的理论进路,进而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老子与孔子哲学理论思维虽旨趣有异,但都问道、求道、体道、悟道,在对道的追求和体悟中,开出不同的路向和新生面。
如果说老子开出道常无有的形而上境界,那么孔子则开出孔颜之乐的人生境界。《论语》载孔子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这就是为后世称道的孔颜之乐。孔颜之乐所乐何事,一直是中国哲人很有兴趣的话题。尤其到宋明理学阶段,孔颜之乐几乎成为贯穿理学体系的核心问题。本文拟从文明发展与情感文化的角度切入,来谈孔颜之乐的精神境界。首先要明确的是,这种境界的产生和发展、理论和实践,都是建立在中国独有的礼乐文明基础之上的。
一、从巫术文化到礼乐文明
中华民族五千年光辉灿烂的文明,一直延续至今。她大化流行,为道屡迁,唯变所适,生生不息。八千年前已迈入农耕文化,相当于考古学上的兴隆洼文化、磁山文化、裴李岗文化、河姆渡文化、彭头山文化。三皇五帝的出现,相当于考古学上的仰韶文化、良渚文化、红山文化。前夏王朝健立,形成独特的一体的“联邦式”中国。在“协和万邦”理念的指导下,从五帝到夏、商、周三代,从文武周公到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中华境内的各民族凝聚出“共识中国”的观念。这一共识位育了光彩夺目、独具特色的中华文化,形成了不断创新、钩深致远的中华型的世界观念、价值观念,构建了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哲学理论、思维方式,呈现了尽精微而能笃行的人生观、伦理观、道德观。
中华民族原始宗教大致经历了自然崇拜、鬼魂崇拜、生殖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等方面,体现出多元性和多样性。随着“联邦式”整体性、统一性国家的建立,实施了“绝地天通”的宗教改革,结束了“民神杂糅”“家为巫史”的时代,民众原有的与神直接交流的权利被取消。颛顼(一说为帝尧)“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由国家委任职业巫师,“在女曰巫,在男曰觋”,掌管神权,这样便由“家为巫史”转化为国家的巫史。《尚书》载:“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这是描述黄帝与蚩尤(传说为苗民首领)的战争给人民造成祸灾和痛苦,带来社会动荡,但文中对“绝地天道”语焉不详。《楚语》记载,楚昭王问观射父:“《周书》所谓重黎实使天地不通者何也?对曰:‘非此之谓也。古者民神不杂。’”韦昭注:“杂,会也。谓司民、司神之官各异。”远古时代民、神交通交流有序,神人各司其职,人民安身立命。后因“九黎乱德”,破坏了宗教制度,人人为巫师,家家与神交通,侵犯了神的权威,社会无序。“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韦昭注:“绝地民与天神相通之道。”于是颛顼命南正重大臣司天,管理宗教事务,命令火正黎大臣司地,管理人间事务。由此割断了人与神直接交通的权利,这便是“绝地天通”的意蕴。虽《尚书》与观射父的论说稍异,但总体意思相似。
中国巫术文化由来已久,早期宗教活动就有巫师。巫,见于甲骨、金文。《说文》:“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周易·巽·九二爻辞》:“巽在床下,用史巫纷若,吉,无咎。”荀爽曰:“史以书勋,巫以告庙。纷,变。若,顺也。谓二以阳应阳。”程颐曰:“史巫者,通诚意于神明者也。”古代医师也称巫。《论语》载:“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皇侃义疏曰:“南人,南国人也。无恒,用行无常也。巫,接事鬼神者。医,能治人病者。南人旧有言云:人若用行不恒者,则巫医为治之不差,故云不可作巫医也。卫瓘云:‘言无恒之人乃不可以为巫医。巫医则疑误人也,而况其余乎。’”程树德集释载:“《礼记·缁衣篇》:‘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为卜筮。”’古人之遗言乎?彼言卜筮,此言巫医,其义一也……故孔子思见有恒者。无恒之人巫医弗为,信矣。”巫、医,古代通称,医师称巫师,医亦巫。康有为说:“巫所以交鬼神,医所以治疾病,非久于其道,则不能精,故《记》曰:‘医不三世,不服其药’,欲其久也。太古重巫医,故巫医之权最大,埃及、犹太、印度、波斯皆然。犹太先知即巫也,耶氏则兼巫医为大教主矣。盖巫言魂而通灵,医言体则近于人,其关系重,故孔子重之,欲其有恒而致精也……巫医皆以士为之,世有传授,故精其术,非无恒之人所能为也。”交鬼神与治病相兼,是一些国家的普遍现象。古人认为人的生死、寿夭、祸福、贫富、贵贱冥冥中由天神主宰、支配,人身的疾病也由天神管控,因而巫与医是从两方面保证人的生命安全、完满、健康、吉祥。所以何休注《春秋公羊传》曰:“巫者,事鬼神祷解以治病请福者也。”事鬼神原为治病、请福,这便是巫医的功用和价值。
巫术文化是中华民族资始资生文化的土壤。在巫术文化的激荡下,先民的心理、情感、知识、智慧、审美意识得以萌生。秉承着朴素和原始的科学和哲学思维,中华先民编纂出占卜之书“三易”,其中之一就是后世所称的《周易》,它逐渐由占卜发展出一整套哲学思想,成为中华民族多源一体文化的源头活水。可以说,中国哲学的突破从《连山》《归藏》《周易》起始。在公元前的11世纪之前,夏、商末年的夏桀、商纣淫欲无度,致使社会动乱,百姓无法生活,人与社会的冲突、人与人的冲突非常尖锐,社会秩序岌岌可危。号称天之代表的的天子夏桀、商纣,暴虐无度,胡作非为,无法无天,削弱了天的至高无上性和绝对权威性,损害了人对天的绝对敬畏威、尊崇感,信仰感。如果说商汤讨伐夏桀的暴政是“替天行道”的话,那么周武王吊民伐罪于商纣,不仅仅体现出“天命靡常”,更重要的是想以此说明,天要授命什么样的人来治理天下。天的要求是“惟德是辅”,即天要授命于能实行德政的有德的君主;君主“以德配天”,才能获得天的授命。君主有德无德的尺度就在于能否保民。因此“敬德保民”便成为永保天命的关键,这便构成“惟德是辅”→“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的互动的逻辑结构。天的唯一性、绝对性转变为天、德、民的多元性、相对性。周人认为夏桀、商纣之所以不能祈天永命,就在于没有体认天、德、民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没有实践祈天永命的德性,这是夏商之所以灭亡的根源所在。周公等人从现实的、历史的实践中体认到这三者之间的互动逻辑关系,以此来化解当时氏族与氏族、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严重的对立和冲突,以此来维护社会、国家、家族的稳定、团结、和谐。
如果说天、民对君主统治集团来说是外在的、客体性的,在一定程度是不能以君主集团的意志所支配的,那么,德则是主体性的、内在性的,因此成为祈天永命的关节点。这种变化,颠覆了巫术文化唯神是从,君权完全由外在的、客体的天所赋予的旧观念、旧价值,巫术文化已不能论证夏桀、商纣君权神授的合理性、合法性,亦颠覆巫术文化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并激发了天命观、国家观、君主观、价值观的转变。于是周公唯变所适,损益夏商礼乐,“制礼作乐”,由此便开启了以礼乐文化为主导代替以巫术文化为主导的哲学思想的转变。
礼见于甲骨、金文。《说文》:“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丰,丰亦声。”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按:“以言事神之事则为礼,以言事神之器则为丰,以言牺牲玉帛之腆美则为丰,其始实为一字也。”按:丰,即豐,为醴初文,为祭、享之酒醴,作器。徐灏注笺:“礼之言履,谓履而行之也。礼之名,起于事神。”礼起源于事神,原义是指敬神、祭神以致福。关于礼的功用与价值,《左传》记载:“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认为礼可以经国理政,稳定社稷,使百姓秩序井然,有利于族群的繁衍生息。《礼记·曲礼上》:“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这四者是礼的功能和意义。
乐见于甲骨、金文。《说文》:“乐,五声八音总名。象鼓鞞。木,虡也。”罗振玉《增订殷墟书契考释》:“从丝坿木上,琴瑟之象也。或增白以象调弦之器……借泺为乐,亦从㕖。许(慎)君谓象鼓鞞,木,虡者,误也。”乐为音乐,《广韵·觉韵》:“乐,音乐。”《周易·豫·象传》:“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郑玄曰:“犹人至乐,则手欲鼓之,足欲舞之也……王者功成作乐,以文得之者作籥舞,以武得之者作万舞,各充其德而为制,祀天帝以配祖考者,使与天同飨其功也。”先王制作音乐,歌功颂德,用来进奉上帝,献于祖宗。程颐注曰:“坤顺震发(豫卦坤下震上),和顺积中而发于声,乐之象也。先王观雷出地而奋,和畅发于声之象,作声乐以褒崇功德,其殷盛至于荐之上帝,推配之以祖考。殷,盛也。礼有殷奠,谓发也。荐上帝,配祖考,盛之至也。”雷上地下,为顺动之意象,蕴和顺豫乐之意义。这体现了以上帝和祖宗为核心的宗教理念。
乐为喜悦、快乐。《广韵·铎韵》:“乐,喜乐。”《集韵·铎韵》:“乐,娱也。”《诗经》载“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湛。宜尔室家,乐尔妻帑。是究是图,亶其然乎。”郑玄笺:“族人和则得保,乐其家中之大小。”夫唱妇随,犹琴瑟合鸣相和。兄弟感情融洽,合家其乐陶陶。家庭和乐,精打细算,是持家之道。这是普通百姓之乐。范仲淹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君子之乐,先忧后乐,乐为快乐、喜悦,喜悦是与喜好相近。《广韵·效韵》:“乐,好也。”《集韵·效韵》:“乐,欲也。”《孙膑兵法》载:“然夫乐兵者亡,而利胜者辱。兵非所乐也,而胜非所利也。”轻率好战的人,会导致国家灭亡;一味贪求胜利的人,会受挫被辱。《诗经》载:“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逝将去女,适彼乐国。乐国乐国,爰得我直。”“逝将去女,适彼乐郊。乐郊乐郊,谁之永号。”郑玄笺:“逝,往也,往矣,将去女与之诀别之辞,乐土有德之国。”发誓从此离开你,到那安居乐业的地方,那理想安乐的去处,所得东西归自己。美好的所在,谁还会长叹呼号?劳动者反对犹如硕鼠一样的剥削者,向往美好安乐的地方生活。
自周公制礼作乐后,礼乐便渐成为主导的文化意识。孔子说:“立于礼,成于乐。”朱熹注:“礼以恭敬辞逊为本,而有节文度数之详,可以固人肌肤之会,筋骸之束。故学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事物之所摇夺者,必于此而得之。乐有五声十二律,更唱迭和,以为歌舞八音之节,可以养人之情性,而荡涤其邪秽,消融其渣滓。故学者之终,所以至于义精仁熟,而自和顺于道德者,必于此而得之,是学之成也。”礼乐既可以使人自立,也可以使人完善;既可以使人“恭敬辞逊”“节文度数”,也可以养育人的情性,荡涤邪秽的念头。这是学者的“中”与“终”,既能卓然自立不动摇,亦能义精仁熟,和顺于道德。
孔子和朱熹阐释了礼乐的内涵、作用、功能、价值以及如何“立于礼,成于乐”。然而礼与乐如何产生,何以起始,必须研究。荀子诠释说:“礼起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而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以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以长,是礼之所起也。”人都有欲望,欲望得不到满足,便有所要求,要求没有一定的限度和界限,就不能不争斗,有争斗便会动乱,动乱就会造成穷困。先王为了化解动乱,维持秩序,于是制定礼义,分出等级,以调整人的欲望,满足人的要求,使人的欲望不至于因物资的不足而得不到满足,使货物也不至于因人的欲望而用尽,物资与欲望互相制约,长久地保持协调和谐。这便是礼的起源。礼与自然物质资源、社会的结构、人的欲望要求、道德伦理密切相关。
“立于礼,成于乐”,那么,乐如何生?何以起始?“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乐则必发于声音,形于动静,而人之道、声音、动静、性术之变尽是矣。故人不能不乐,乐则不能无形,形而不为道,则不能无乱。先王恶其乱也,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以乐而下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諰,使其曲直、繁省、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使夫邪污之气无由得接焉。”音乐是人的喜乐感情的表现,这是人的情性所不可缺少的,所以人不能没有音乐。人有喜乐的感情,就一定会流露于声音中,体现在动静上,做人的道理和思想感情的变化都表现在音乐中。先王制定雅与颂乐曲,加以引导,使其不流于淫乱,使乐章辨清乐曲的含义,使声音张弛有度,富有美感,以唤起人心的善良,使邪污之气无法存在。这是先王制乐的原则与目的。
礼乐的端始、构建,都是为了化解人性中的邪念和淫思、行为中的贪暴和动乱,激发起人的善心,而至于真、善、美的境界。在孔子与宰我“三年之丧”的问答中,宰我认为三年居丧守孝太长了:“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但从亲情上说,孔子认为儿女生下三年才脱离父母的怀抱,居丧守孝三年是应然的,居丧期间可以更深刻地怀念父母的功绩、人格、道德、精神,以便继承发扬。这并不会导致礼崩乐坏的局面。礼也分等级。季氏作为鲁国的大夫,却僭用天子之礼,“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皇侃义疏:“马融曰:‘孰,谁也。佾,列也。天子八佾,诸侯六,卿大夫四,士二。八人为列,八八六十四人也。鲁以周公故。”“天子用八,以象八风。八风者,八方之八卦之风也。北曰广漠风,东北曰条风,东曰明庶风,东南曰清明风,南曰景风,西南曰凉风,西曰阊阖风,西北曰不周风也。六,礼降杀以两。天子八佾,诸侯故六佾也。”杜预注:“《春秋》及《公羊传》皆云:诸侯六六三十六人,大夫四四十六人,士二二四人也。’”礼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诸如典章制度、治国方略、伦理道德、行为规范、祭祀鬼神等。“礼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国而无礼,譬犹瞽之无相与,伥伥乎其何之!譬如终夜有求于幽室之中,非烛何见!若无礼,则手足无所措,耳目无所加,进退揖让无所制,是故以之居处,长幼失其别,闺门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猎戎事失其策,军旅武功失其制,宫室失其度,量鼎失其象,味失其时,乐失其节,车失其式,鬼神失其飨,丧纪失其哀,辨说失其党,官失其体,政事失其施,加于身而错于前,凡众之动失其宜,如此则无以祖洽于众也。”郑玄:“见言失者,无礼故也。策,谋也。祖,始也。洽,合也。言失礼无以为众倡始,无以合和众。”礼犹如幽室的烛光,是瞽者相扶的向导。如果没有礼,人们便处在黑暗之中,找不到方向。对于治理来说,礼是不可缺的动力,并且具有普遍性;对于人来说,举手投足、洒扫进退都要遵守礼,若无礼就没有秩序了。从范围来看,政事、戎事、宫室等都要按礼去做;从制度来说,量鼎、车舆、祭祀等均尊礼仪。如果凡事失礼,那么便无法让大家和谐相处。孔颖达疏:“每事如此,则为君上失德,不可为众人之倡始而使和合者也。”凡事以礼来治理,使社会、国家各方面都能达到孔颜之乐的和合境界。
如果说礼能使社会和国家事事有序,是一种外在的使人必须遵守规则的力量,那么乐则是一种内在的的激发人的情感、善心、和谐的心灵的力量。《乐记》曰:“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啴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于物而后动。”乐的本源在于人心,人的主体心与客体物相感应,化生不同心情,哀心、乐心、喜心、怒心、敬心、爱心与外物相感应,便产生各种声音。这多元乐声,直通向伦理。“先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这是制礼作乐的宗旨。只有如此,才能实现“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礼乐刑政四者俱备,通行四方,不会违反正道。乐之所以具有“反人道之正”的效能,是因为乐“在宗庙之中,闺门之内,乡里族长之中”。君臣、父子、兄弟、长少同听,便能感动人的心灵,使人和敬、和亲、和顺。“故乐者,审一以定和者也,比物以饰节者也。合奏以成文者也,足以率一道,足以治万变。是先王立乐之术也。”梁启雄按:“孙希旦曰:一者,谓中声之所止也。《左传》:‘先王之乐所以节百事也,故有五节迟速本末以相及,中声以降,五降之后,不容弹矣。于是有烦乎淫声,慆堙心耳,乃忘平和。’盍五声下不踰宫,高不过羽,若下踰于宫,高过于羽,皆非所谓和也。故审中声者所以定其和也。然五声皆为中声,而宫声乃中声之始,其四声者皆由此而生,而为宫声之用焉。则审中声以定和者,亦审乎宫声而已。此所以谓之一也。比,合也。审一以定和,而以之上下相生以为五声,而又比合于乐器以饰其节奏也。”乐要定一个中音作为基本音,以此来确定乐调的,然后配上各种乐器,调整节奏,一起合奏,构成一支和谐的乐曲。乐足以透露为人的根本道理,足以调整人们各种思想感情的变化。“且乐也者,和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合同,礼别异。礼乐之统,管乎人心矣。穷本极变,乐之情也;著诚去伪,礼之经也。”音乐体现着和合一致的根本原则,礼体现着等级制度的根本原则。音乐使人们达到和谐和合,礼仪使人们区分为上下等级。礼乐合在一起,可以收束人心。从根本上改变人的性情,具乐的本质;以诚心去虚伪,是礼的原则和常经。礼乐文化潜移默化了人的性情节操、伦理道德、行为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情趣,而导向孔颜之乐的精神境界。
中国传统的文化模式可以称之为“乐感文化”,这是与西方“罪感文化”相比较而言的。相对应的,中国传统的情感模式可以称为“乐感情感”。人是有情的和合存在。何为情?中国传统哲学所说的情与西方所说有别。汉许慎《说文解字》:“情,人之阴气有欲者。从心,有声。”徐灏注笺:“发于本心谓之情。”如人的喜、怒、哀、惧、爱、恶、欲七情。王充解释说:“情,接于物而然者也,出形于外,形外则谓之阳,不发者谓之阴。”情犹阴阳之气的流动,若心灵发动情而表现于外,为阳;不发动、不流行、不与外物相接触,为阴。分析与情相关的一系列概念,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哲学中情的内在含义。
第一,情状与情态。这是指事物或人的状态、形态、态度或情形。《周易》曰:“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故不违。”虞翻注:“乾神似天,坤鬼似地。圣人与天地合德,鬼神合吉凶,故不违。”魂是流动的情状,乾神的精气流于坤体,变成万物的情状。天人合德,其情状与天地相似,所以无所差违。韩康伯注:“精气絪缊,聚而成物,聚极则散,而游魂为变也。游魂,言其游散也。尽聚散之理,则能知变化之道,无幽而不通也。德合天地,故曰相似。”虞翻、郑玄等以象数解《易》,韩康伯以义理解《易》。两者虽有差分,但解字义差分不远,都认为是一种变动的情状、情态。指人的情状的例子,如《三国志》载,胡质在黄初年间(220-226年)迁任东莞,士人卢显为人所杀,质曰:“此士无仇而有少妻,所以死乎!悉见其比居年少,书吏李若见问而色动,遂穷诘情状。若即自首,罪人斯得。”胡质追问中,李若脸上神色有变化,情态也有异状,随后就自首了。又韩非曰:“人主欲见,则群臣之情态得其资矣。”君主有所厌恶,群臣就把他所恶的隐匿起来。君主有所爱好,群臣就会弄虚作假来迎合他。君主的欲望表现出来,群臣就会借此呈现自己的情态。若君主无好恶,群臣就不会为伪。君主应该去好去恶,群臣诚实质朴,君主就不会被蒙蔽了,关于情态的真相就不会被隐匿了。
第二,情趣与情致。这是指人的志趣、志向、兴趣、意愿、欲望、风致所在。《后汉书》载,刘陶“为人居简,不修小节。所与交友,必也同志,好尚或殊,富贵不求合,情趣尚同,贫贱不易意”。结交的朋友,都是志同道合者,志趣不同,即使是富贵的人,也不去交好;情趣相同,即使是贫贱的人,也不改变意向。这就是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情趣。关于情致,颜之推引《诗》曰:“《诗》云:‘萧萧马鸣,悠悠旆旌。’毛《传》曰:‘言不谊哗也。’吾每叹此解有情致,籍诗生于此耳。”王籍有才气,好学博涉,他的《入若耶溪》诗有“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句,其情致出于《诗》的风致。唐代张籍的《和左司元郎中秋居十首》之四:“山晴因月甚,诗语入秋高。”其情其致,堪称高雅。
第三,情谊与情礼。情谊是指人与人之间的交情。如韩愈《与崔群书》说:“与足下情义(作谊),宁须言而后自明邪。所以言者,惧足下以为吾所与深者,多不置白黑于胸中耳。”韩愈认为崔群出类拔萃,作为朋友,明白彼此深厚的情谊,不曾疑惑于心。有情谊而讲礼节,讲礼节而有节操品德。人若无节操品德,也不会有情谊和礼节。《晋书》载:康帝司马岳下诏:“昔先朝政道休明,中夏隆盛,山、贾诸公皆释服从时,不获遂其情礼。况今日艰难百王之弊,尚书令礼已过祥练。岂得听不赴急疾而遂罔极之情乎!”时荐顾和为尚书令,顾和以母居丧,表疏十上,遂不赴职,服丧毕,然后视职。中国古代对丧礼很重视,官员务必辞职居丧,所以顾和居丧期间不接受官职是符合情理的。若丁母忧而不辞职居丧,是要受到社会普通谴责的。
第四,情思与情欲。这是思念、想念而不忘怀,也是一种欲念、欲望。《庄子》载:“以禁攻寝兵为外,以情欲寡浅为内。其大小精粗,其行适至是而止”这是说,对外是禁止攻伐停止战争,这是利他;对内是减少欲望,这是自利。“自利利他,内外两行,虽复大小有异,精粗稍殊,而立趋维纲,不过适是而已矣。”
第五,情理与情义。这是指人情与事情的道理、义理,以及事物发展的规则。《世说新语》载:“王刘听林公讲。”注引《高逸沙门传》:支遁“正在高坐上,每举尘尾,常领百言,而情理俱畅。预坐百余人,皆结舌注耳。”支遁讲佛理,情理明白通畅透彻,言辞逻辑严密,听者专注而感人。之所以感人,是因为其释义理符合情理,具有感染力。
第六,情感与民情。西方一些哲学价值观念认为,以智慧为特色的哲学,为建构理性的权力,需要把情感因素排斥在外。尽管康德为限制理性权威而提出情感与意志话题,不过情感为心理经验,而非形而上的超验话题。但中国哲学是人的哲学,人是什么,人何以为人,这是中国哲学各学派所共同关注的重要话题。人是有情感的存在者,这种情感甚至可以影响天道的选择。《尚书》载:“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见。”孔安国传曰:“天德可畏,以其辅诚人情大可见。”这是把人民的情感作为天是否诚心辅祐的标准。《左传》庄公、僖公、哀公所载的情,是指实情,实际真实的情况。《论语》载:“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皇侃义疏:“君上若信,则民下尽敬不复欺,故相与皆服于情理也。李充云:‘用情,犹尽忠也。行礼不以求敬,而民自敬。好义不以服民,而民自服。施信不以结心,而民自尽信。言民之从上,犹影之随形也。’”朱熹曰:“礼、义、信,大人之事也。好义,则事合宜。情,诚实也。敬、服、用情,盖各以其类而应也。”君主喜好礼、义、信,百姓自能尽礼、义、信。
关于情感的感,《说文》载:“感,动人心也。从心,咸声。”感与情密切相关,亦包括几种含义,值得做一辨析。
第一,感动与感应。《周易·咸·彖》载:“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王弼注:“二气相与乃化生也。天地万物之情见于所感也。凡感之为道,不能感非奏者也,故引取女以明同类之义也。同类而不相感应,以其各亢所处也。故女虽应男之物,必下之而后取女乃吉也。”孔颖达疏:“圣人设教感动人心,使变恶从善,然后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者,结叹咸道之广大,大则包天地,小则该万物。感物而动,谓之情也。天地万物皆以气类共相感应,故观其所感物而动谓之情也,天地万物皆以气类共相感应,故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天地万物相互交感,澄明万物的情性。如果同类不相感应,是因为其相亢的不和谐关系。
第二,感触与触碰。主体的眼耳鼻舌身与客体的物、事相接触、碰撞,而产生感应、感慨、感叹。晋陶潜《归去来兮辞》:“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感慨自己生命和生活的欢乐、吉庆。《北史》载,刘璠字宝义,九岁而孤,居丧合礼。周文“以璠为中外府记室,迁黄门侍郎、仪同三司。尝卧疾居家,对雪兴感,乃作《雪赋》以遂志焉”。卧疾居家,摆脱政事,欣赏自然景色,对雪产生感兴而作赋。兴是心与物偶然相遇,即主体心与客体物相接触,并为托事于物的一种隐喻。《周礼·春官》以“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为六诗,于是赋、比、兴相连。“托事于物”是指以景物言人事及以他物言此事。刘勰《文心雕龙·比兴》篇说:“观夫兴之托喻,婉而成章,称名也小,取类也大。”兴可以委婉含蓄,以小喻大。兴以起情,有感触而发。《庄子》载:“睹一异鹊自南方来者。翼广七尺,目大运寸,感周之颡,而集于栗林。”成玄英疏:“盛,触也。颡,额也。”庄周游于栗园蔺篱之内,额头触到聚集于栗林的鹊,这也称之为感。
第三,感受与思念。人生活在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宗教、意识的结构之中,须臾不离。人身处其中,生理和心理都时时刻刻感受到外在环境的影响。《黄帝内经》载:“清风大来,燥之胜也。风木受邪,肝病生焉。热气大来,火之胜也。金燥受邪,肺病生焉……所谓感邪而生病也。乘年之虚,则邪甚也。失时之和,亦邪甚也。遇月之空,亦邪甚也。重感于邪,则病危矣。”这是说人的身体感受外在邪气而生病,其实是在讲环境致人生病的情况。环境包括自然条件,如所谓清气、热气、寒气、风气、湿气,也包括人事变化。《北史》载:刘璠忽一日全身楚痛,一会儿家信送到,说其母病。他号泣戒道,绝而又苏。“居丧殷瘠,遂感风气,服阕后一年,犹杖而后起。”闻母亲病,哭得昏过去,其悲痛情感可感知。在守丧期间,身体十分瘦弱,服丧终了以后,才能扶杖站立起来。又《后汉书》载:“周能感亲,啬神养福。”李贤注:“感,思也。谓诵《诗》至《汝坟》,思养亲而求仕也。啬神养福谓不应辟召,以寿终也。《左传》曰:‘能者养之以福。’”感亲就是思念亲人。
人的情感是复杂的。在理智与情感的相持相待中,使情感处于中和状态,这是中国乐感情感的特色,而与西方酒神情感、罪感情感大相异趣。《旧约全书·创世纪》载,神创造天地及世间的一切万物,从星期一到星期五就完成了。星期六,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样式造人,造男造女。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神曾说,伊甸园中的树上果子可以喫,唯有智慧树上的果子不可摸、不可吃。然而,夏娃听了蛇的引诱,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子,也给她丈夫亚当吃了。他们的眼睛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一天神到园中,夫妻二人就藏在树木中,躲避神。因为他们违背了神的话和意志,于是神罚蛇用肚子行走,并与女人及其后裔为仇。罚女人承受怀胎的苦楚,并罚亚当终身劳苦。神把亚当和夏娃赶出伊甸园。由于人的始祖亚当和夏娃背离神而犯有元罪,于是西方永续着罪感情感。
罪感情感从人性恶出发,尊崇一元的神,上帝。上帝意志就是真理,不可违反、背离,否则就要受到惩罚。乐感情感从人性善出发,求道、问道、悟道于自然、社会、人生实践,产生多元、多样的体悟和感受。这就是乐感情感与罪感情感的分野。
四、孔颜之乐的境界
乐感情感的乐,是主体心与客体事物相遇的审美融合中所获得的美感情感的体验。“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皇侃曰:“亦,犹重也。悦者,怀抱欣畅之谓也。言知学已为可欣,又能修习不废,是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弥重为可悦。”悦是内在心灵的喜欢。学了新知识,时时诵习而不废,这是很高兴的事。有志同道合的朋友从远方来,不也很快乐吗?这是读书、诵习、会友等日常生活经验感性情感的体验。这种快乐,既是经验感性,又超越经验感性;既是世间性的乐,又是精神性的乐;既是已乐,又与他人同乐。因此,此乐具有普遍的意义。这种超经验性、精神性、普遍性的乐,在孔子与弟子交流时也时有表露。
《论语》载,孔子与子路、曾点、冉有、公西华四人谈论人生的志愿爱好与治国理政等。子路、冉有、公西华三人谈完志向后,孔子问曾点(曾参的父亲)的志向。曾点说:“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皇侃曰:“不云季春而云暮春者,近月末也。月末其时已暖也。‘春服成’者,天时暖,而衣服单袷者成也……暮春者既暖,故与诸朋友相随,往沂水而浴也……祭而巫舞,故谓‘舞雩’也。沂水之上有请雨之坛,坛上有树木,故入沂浴出登坛,庇于树下,逐风凉也。故王弼云:‘沂水近孔子宅,舞雩坛在其上,坛有树木,游者讬焉’也。浴竟凉罢,日光既稍晚,于是朋友咏歌先王之道,归还孔子之门也。”暮春季节,春天的衣服穿好了,和同伴在沂水洗澡,在祭坛上吹风乘凉,唱着歌回来。孔子叹气说赞同曾点的主张。这是自由潇洒的精神境界。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在《论语集注》中说:“曾点之学,盖有以见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少欠缺……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于言外。”认为曾点所言的是去除人欲、天理流行的从容境界,并将其升华为悠然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的与天地、与万物、与神合一的状态。
朱熹彰显曾点的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融合的形而上的境界,超越了天地万物,是一个体道的境界。人们问道、体道、悟道,通常是饿其体肤、劳其筋骨而后才能有所成就的。孔子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皇侃曰:“美颜回之贤行。”“食不重餚,及无彫之器。”“美其乐道情笃,故叹始末言贤也。”由于求道,乐道,所以箪食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但颜回久而不改其乐。外在的穷困,都不能动摇和干扰其情笃于乐道的信心和决心。朱熹引程颐话说:“昔受学于周茂叔,每令寻仲尼、颜子乐处。”孔颜乐处,其关键就在于乐道之乐。为道不仅可放弃物质生活的一切享受,甚至可牺牲自己的生命。这种乐感情感是高尚和伟大的。
永无止境的求道、问道、悟道,其理论思维便具有多元性和开放性。因其多元性和开放性,儒家才构建起孔颜之乐的博大的境界。“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皇侃曰:“智者,识用之义也。乐者,贪乐之称也。水者,流动不息之物也。智者乐运其智化物,如水流之不息,故乐水也。”“仁者,恻隐之义;山者,不动之物也。仁人之性,愿四方安静如山之不动,故云乐山。”智者动,“智者何故如水耶?政自欲动进其职”,“其心宁静故也。”智者乐,“乐,欢也。智者得运其职,故得从心而畅,故欢乐也。”“性静如山之固,故寿考也。然则仁既寿亦乐,而智乐不必寿,缘所役用多故也。”智仁不离不杂,不离而合一,不杂而分二;智仁即体即用,即用即体。智喜好融摄万物的事理,周流不息犹如水;仁犹人的道德本性,安于义理如不动的山,无欲故静。智者从心所欲,心情通畅而欢乐;仁者德性清静,所以长寿。积善修身,形神以和,为仁者寿之本。乐山乐水是物化人,是人的自然化;智仁是人化物,是物的道德理性化。而孔颜之乐是乐道,是人的生命度越化的升华,超越肉体生命,而赋予道德生命、价值生命,真善的生命。这才是孔颜之乐要追求的境界。
孔颜之乐,是超越世俗之乐,是高尚求道的乐,是不问生死之乐。“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皇侃曰:“谓孔子慨世道之不行,故发愤而忘于食也。又饮水曲肱,乐在其中,忘于贪贱之忧也。又年虽耆朽而信天任命,不知老之将至也。”孔子愤慨世道弊病,所以发愤用功,沉浸于求道的乐趣,连吃饭都忘了,甚至忽略了自己的年岁。“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皇侃曰:“言孔子食于菜食而饮水,无重肴方丈也……言孔子眠曲肱而枕之,不锦衾角枕也。孔子粗食薄寝,而欢乐怡畅,自在粗薄之中也。”朱熹注:“圣人之心,浑然天理,虽处困极,而乐亦无不在焉。”吃粗粮,喝冷水,弯着胳膊做枕头,也有乐趣。孔子度越世俗生活理念,心中纯然天理,而无一毫私欲;度生死于身外,老之将至,死之将来,不改其乐,不求肉体生命之乐,而求道德生命、价值生命的不朽之乐,并进入审美的艺术境界。“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皇侃曰:“《韶》者,舜乐名也,尽善尽美者也……齐是无道之君,而滥奏圣王之乐,器存人乖,所以可伤慨也。”孔子到了齐国,听到齐国君主让人奏《韶》乐,孔子赞叹尽善尽美中,想不到欣赏音乐的快乐到了这种境界。乐随人君而变者,如周文武王遍奏六代的乐,当周公、成王、康王时,六代的声悉善,亦悉以教化民众。所以《韶》乐在齐,其音犹有盛美的情感,充盈孔颜之乐的精神美。
冯友兰说:“天地境界有四个层次———知天,事天,乐天,同天。我这个说法也是参考孔子的自述得来的。‘五十而知天命’就是‘知天’。‘六十而耳顺’就是顺天命,也就是‘事天’。‘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就是说,到了七十之年,他‘从心所欲’,就自然合于‘四德’的规范,这就是‘同天’,也就是所说的‘圣与仁’……孔子的自述,没有提到‘乐天’,但是《论语》记载他讲‘乐’的地方有很多。讲到他自己的生活时,他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他又赞美颜渊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雍也》)孔子和颜渊所乐的,并不是那种贫苦的生活。现在的人们,常说‘以苦为乐’,其实苦就是苦,怎么能以之为乐呢!孔子在这两段话中所说的‘乐’,其实就是‘知天、事天、同天’的那种精神境界。后来的道学家周敦颐教他的学生:‘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可以说他认识到了孔子的要点。”乐山乐水,乐而忘忧;乐于求道、问道、悟道,从而构建起孔颜之乐的人生境界。孔颜之乐的人生境界是一种道德高尚、博学明辨、胸襟坦荡、感情真实、意志坚强、心灵美好的境界,是圣贤精神境界。
【作者】张立文,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
本文刊于《中州学刊》2023年第10期,参考文献及注释参见原文。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