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开亮:儒家伦理—政治美学与当代美育理论的建构
日期:2019-11-07摘要:儒家“美善关系”呈现了儒家对“美”的语义的独特理解。儒家“美善合一”的综合形态之美不同于现代美学的单维度之美,而是一种内置了“道德善”的古典伦理—政治美学。在当代美学视域中,这种伦理—政治美学依然具有理论的有效性与正当性。以伦理-政治美学为参照,可以消除现代美学体系带来的美育理论困境,使当代美育的性质以及美育与德育的地位问题获得一种更合理的解答。
关键词:美善合一;伦理—政治美学;美育;德育
儒家哲学作为一种“为己”的人生哲学,其最高的文化目标是要去实现一种理想的道德君子人格以及由此道德君子人格组成的仁政社会。因此,审美与道德、审美与政治的美善张力一直固存于其教化哲学中。在当代关联型美学背景下,探讨具有鲜明美育色彩的儒家“美善合一”的伦理—政治美学既有利于树立中国美学话语、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又可为当代的美育理论建构提供有效的理论资源。
一、儒家“美善关系”论与古典伦理—政治美学
在中西美学史上,审美与道德、政治或者“美善关系”一直处于一种复杂的态势之中。一般而言,美善相一致模式为中西古典美学和艺术理论所首肯,而美善相分离模式则为现代美学和艺术理论所推崇。由于中国哲学奠基于主客不分的世界观与知情意相统一的人性观上,儒家“美善关系”相较于西方的古典美学理论,还有着自身的独特性。
在西方古典美学和艺术理论中,美善相一致的说法可谓由来已久。苏格拉底就曾说:“任何一件东西如果它能很好的实现它在功用方面的目的,它就同时是善的又是美的,否则它就同时是恶的又是丑的。”[1]柏拉图更从政治和道德的角度出发,在其《理想国》中旗帜鲜明地给多数艺术家下了逐客令,要求除了颂神和赞美好人的诗歌外,其他有可能败坏道德的诗人都请他到旁的城邦去,再不准他们闯入国境。在中国传统美学和艺术理论中,同样出现过这种相似的审美功利主义看法。汉代儒家出于经学解释的需要,对中国文化中极为灿烂辉煌的《诗三百》进行了道德与政治诠释的嫁接,使得本来情趣盎然的《诗经·国风》一些篇章被生硬地改造成道德政治教科书并影响了近两千年。这种美善相一致的看法其实是一种以道德、政治来统治和奴役艺术的办法,它把道德、政治看作是审美的外在目的,其注重的核心是道德、政治而非审美,所以在理论方面显得比较粗放。
然而,儒家对“美善关系”的处理并非都是这样。特别是在先秦儒家那里,“美善关系”有着自身丰富的深刻内涵。《论语·八佾》云:“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这里,孔子对“美”与“善”进行了区分,并认可了“美”是具有自身独立价值的。这句话中的“美”的含义指的更多是一种外观形式之美。在孔子看来,《韶》乐比《武》乐更优秀的原因不在于艺术外观形式而在于《韶》乐的内容(歌功颂德、礼乐教化)比《武》乐的内容(述功正名、杀伐之态)更具有道德、政治价值。并且,正是这种道德、政治价值带来了《韶》乐远超于《武》乐的审美体验。同样,《论语·雍也》载孔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难乎免于今之世也。”按杨伯峻注解,孔子这里对外观形式之“美”又进行了嘲讽。[2]特别是,孔子对极具外观形式之美的“郑声”进行了拒斥:“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论语·卫灵公》)一方面是肯定外观形式之美,另一方面又拒斥外观形式之美,对孔子这两种相反的立场合理的解释当是:孔子对“美”的理解并非仅限于单纯的形式外观或者形式主义,而是一种蕴含着道德、政治内容的形式之美。《武乐》“未尽善”只是说“善”不够完备,而不是说没有道德内容或完全偏离了礼。《论语·卫灵公》孔子曰:“乐则《韶》、《舞》。”《舞》即为《武》。《乐记·宾牟贾篇》就专门记述了孔子对《武乐》道德、政治内容的评价。由此可见,孔子对“何为美”的基本语义理解是外观形式与道德、政治内容的相互结合,是一种内容与形式相统一且道德、政治内容能增益审美体验之美。在孔子看来,如果外观形式之美有着一定的道德、政治内涵,那这种外观形式之美就是值得欣赏的;反之,如果仅有单纯的外观形式之美而没有任何道德、政治内涵或者具有的是反道德的内涵,那这种外观形式之美则是令人反感并难以被欣赏的。[3]这种自身就包孕了良善的道德、政治内容并能增益体验的对“美”的理解实与当前美学学科所讲的“感性学”、“情感学”、“形式主义”、“非功利性”、“自律论”等单维度之美有差别,它是在区分美、善的基础上又对美、善进行合一(美中必有善,有善才有美)的古典综合形态的“大美”或伦理—政治美学。“美善合一”构成的一种“大美”或伦理—政治美学方是孔子对“美”的语义内涵。

可以说,孔子对美的诸多领域论述都是围绕着“美善合一”原则展开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这是讲诗之美:情感天真与思想无邪的结合;“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这是讲礼乐之美:礼乐之盛与真挚仁心的结合;“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这是讲人格之美:外表得体与内在品质的合一;“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雍也》)这是讲山水之美:山水之乐与仁智之德的结合;“绘事后素。”(《论语·八佾》)这是讲绘画之美:形象之美与礼的结合;“臧文仲居蔡,山节藻梲,何如其知也?”(《论语•公冶长》)这是讲建筑之美:建筑之丽与政治身份的结合;“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论语·泰伯》)这是讲政治之美:君王气象与政治和谐的结合……儒家后来《孔子诗论》的“诗亡隐志”、《易传·坤•文言传》的:“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孟子·尽心下》的“充实之谓美”、《尚书·舜典》的“诗言志”、《礼记•少仪》的“言语之美,穆穆皇皇;朝廷之美,济济翔翔;祭祀之美,齐齐皇皇;车马之美,匪匪翼翼;鸾和之美,肃肃雍雍”、《乐记》的“乐者,通伦理者也”、《荀子·乐论》的“美善相乐”等美学命题也都无不坚守着“美善合一”这一基本原则。如果剥离掉其间“善”的因素,其美感将是极为稀薄乃至难以想象的。
同情地看,儒家对“美”之综合形态语义的这种理解是与其文化理想相结合的一项重大教育工程。面对正在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僭越礼制仅追求外观形式与感官愉悦的单维度美学新潮正在四处涌动。作为道德理想主义的儒家,一方面看到了这种审美新潮与理想道德、政治相脱离乃至对理想道德、政治进行解构的危险所在。另一方面,儒家也看到了审美的积极意义所在——能够通过引导感官愉悦,可以与良善道德、政治相结合并形成对道德、政治的正面建构力量。针对这种情况,儒家在对那种纯粹的审美进行拒斥的基础上,试图通过在不抹杀审美感官愉悦的过程中又引导审美的道德方向性走向。既要正视人性对审美的需求,又要将之进行积极的引导。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儒家在重视诗乐艺教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形式与内容相统一的文艺观、审美情感与道德理性相结合的情理观来处理“美善关系”,以建构自身的伦理—政治美学形态。由于儒家这种伦理—政治美学形态并没有抹杀审美与情感愉悦,且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美的独立价值,故不能被视为是在以道德或政治代替审美,因而那种把儒家“美善关系”理解为“美即善、善即美”的看法是有问题的。同样,这种“美善合一”论不能被视为一种将审美当作道德与政治工具的审美功利主义,因为儒家“美”的综合形态语义是把道德政治之“善”作为“美”的文艺与情理内容内蕴在其对“大美”的理解中的。内蕴表明“善”是“美”的内在价值与内在目的,功利则仅是将“善”视为“美”的外在价值、外在目的。可以说,儒家“美善合一”的伦理—政治美学观念是一种有着正向价值担当的美好生活之道。
二、作为一种当代美学形态的伦理—政治美学
儒家“美善合一”的伦理—政治美学观念自先秦建立后,一直作为中国古代主流的美学精神影响后世。在“诗言志”、“美刺比兴”、“自然即名教”、“文以明道”、“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文以载道”等观念中,都渗透着古人对这种古典美学的认同。然而,从上世纪初开始,由于这种与善一体的美学观与西方现代美学的“非功利性”观念相冲突,渐趋遭到了现代学人的批评。
西方现代美学观念注重审美自身的独立性,将审美更多视为一种与道德、政治无关的非功利性独特经验。现代主义美学代言人之一的克罗齐就说:“善良的意志能造就一个诚实的人,却不见得能造就一个艺术家。既然艺术并不是意志活动的结果,所以艺术便避开了一切道德的区分,倒不是因为艺术有什么豁免权,而是因为道德的区分根本就不能用于艺术。”[4]受现代美学影响,王国维就曾对古代诗歌创作提出过批评:“呜呼!美术之无独立价值也久矣。此无怪历代诗人,多托于忠君爱国劝善惩恶之意,以自解免”、“咏史、怀古、感事、赠人之题目弥满充塞于诗界”。[5]刘若愚更是以“实用的观点”来评价孔子审美观,认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美学更多是一种实用主义宣言。[6]“实用的观点”认为儒家美学仅仅把审美与艺术当作道德、政治的手段,是一种审美实用主义或审美功利主义。于是,在这种现代美学观念中,儒家伦理—政治美学作为一种“前现代”理论,俨然失去了一种现代理论的正当性而成为批驳的靶子。在笔者看来,今天如果要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从传统儒家美学中吸取养分,首先需要论证的就是儒家伦理—政治美学在今天依然具有理论的有效性与正当性。
首先,从现代美学的批驳来说,正如前面所述,用审美功利主义来评价儒家美学的看法是存在问题的。事实上,现代美学批驳的是那种把艺术仅当成道德与政治工具的极端功利主义。这种现代观念自觉地将审美活动从其他社会活动中独立出来,对推动美学的深入研究与促进文艺的发展是具有极大意义的。但是这种批评方式是否有效尚需两个提前条件:其一,儒家伦理—政治美学是否就真的是审美功利主义;其二,现代美学本身是否就是美学存在形态的唯一真理。就第一个前提条件而言,正如前文所辨正的,用审美功利主义来定位儒家“美善合一”美学是不能成立的。儒家并非将道德与政治视为其审美的外在目的,而是一种内在目的。黑格尔说,“一说到目的,一般人心目中总以为只是指外在的合目的性而言。依这种看法,事物不具有自身的使命,只是被使用或被利用来作为工具,或实现一个在自身以外的目的。这就是一般的实用的观点。”[7]黑格尔认为事物除了外在目的还具有内在目的:“在有机体中,目的乃是其材料的内在的规定和推动,而且有机体的所有各环节都是彼此互为手段,互为目的。”[8]按黑格尔内在目的论,儒家伦理—政治美学“美善合一”有机体内,“善”实际是一种儒家“美”论的内在规定和推动,它与美是互为目的而不是美的外在功利性。就第二个前提条件而言,现代美学形态将审美活动从其他社会活动中完全孤立出来,将情感结构从知情意统一的人性中分割出来,既不符合社会活动经验的统一性也不符合人性的完整性。朱光潜在反省自己以前的形式派美学观点时就说:“从前,我受从康德到克罗齐一线相传的形式派美学的束缚,以为美感经验纯粹地是形象的直觉,在聚精会神中我们观赏一个孤立绝缘的意象,不旁迁他涉,所以抽象的思考、联想、道德观念等等都是美感范围以外的事。现在,我觉察人生是有机体;科学的、伦理的和美感的种种活动在理论上虽可分辨,在事实上却不可分割开来,使彼此互相绝缘。”[9]因而,现代美学能否就代表了美学形态存在的唯一真理也是可疑的。
其次,随着当代美学理论的进展,质疑、否定现代美学“审美非功利性”的美学流派开始大量出现。如环境美学把认知与伦理等因素介入进了审美体验、身体美学强化了审美的生理因素、生活美学对审美与生活界限进行了颠覆、政治美学把政治泛化为审美等思潮的出现,都表明当代美学渐趋由现代区分型美学走向一种关联型美学。张法指出:“当区分型美学和关联型美学没有高低等级之分、区分型美学的美学霸权被破除之后,各类美学的独特性才会自由地展现开来,这里,由区分型美学主导的美学全球化,即让各非西方文化的美学都变成具有西方区分型美学特点一样的美学,就会转变成由各大文化美学互动和对话而来的全球化美学,即一种超越西方区分型美学的、把全球各不同文化的美学优点都吸收进来的,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一种新的升华的美学。”[10]关联型美学注重的是审美活动中诸多要素的融合与增进,是将美的呈现方式置于一种与之关联的网络结构当中。正因如此,当代国外很多美学研究者也对美与善、审美与道德这一古老论题又予以了重新的关注。韦尔什(Wolfgang Welsh)、卡罗尔(Noël Carroll)、谢泼德(Anne Sheppard)、高特(Berys Gaut)、舍勒肯斯(Elizabeth Schellekens)等人都使得艺术与道德、美学与伦理学的关系重新获得了曾经有过的重要性。[11]在这种关联型的当代美学视野下,儒家将美善进行关联的古典伦理—政治美学也当迎来一次价值重估与理论重建的时代契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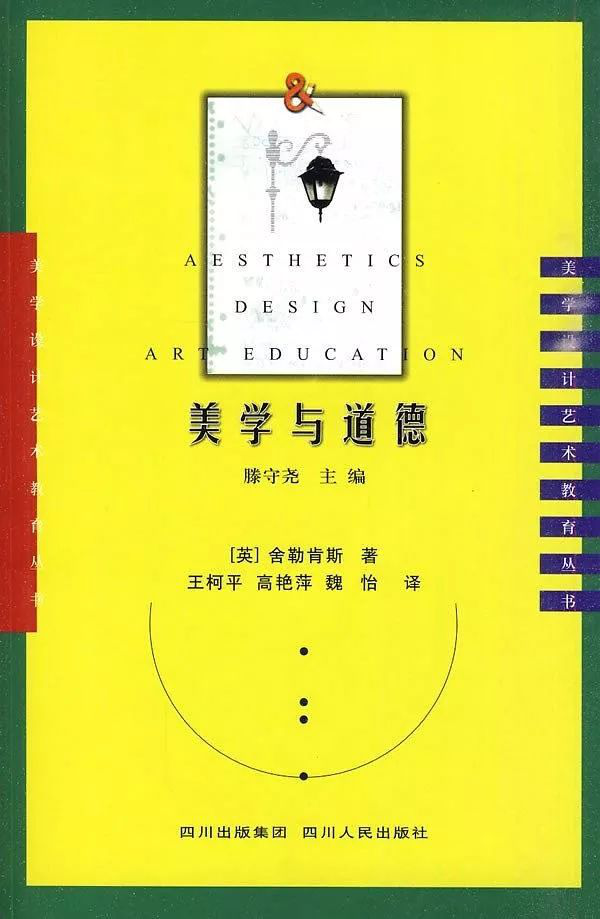
在笔者看来,在儒家“美善合一”原则下,儒家美学有助于建构一种当代美学形态的伦理—政治美学。这种当代形态的伦理—美学在坚持儒家“美善合一”的原则基础上,并应对善的内容、尺度、美善结合方式等做出符合时代性的调整。当代德国美学家韦尔施说:“我将尝试发掘审美自身的伦理潜质,并指出由此而来的某些伦理学后果。‘伦理/美学’(aesthet/hics)这个生造词由‘美学’和‘伦理学’缩约而成,它旨在意指美学中那些‘本身’包含了伦理学因素的部分。”[12]儒家美学与韦尔施的构想是相通的,其在坚持善的时代内涵(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等)基础上完全可以顺利地转化为一种当代美学形态。这种伦理—美学是自身就内蕴了道德与政治因素的美学,故它不是为了伦理、政治的美学,而是道德、政治与审美因素有机结合、内在统一、互为目的美学。为了伦理或政治的美学虽然也讲究审美与道德、政治结合,但这种结合往往是将道德、政治因素暴力植入审美,实际造成了对审美的伤害。孔子就专门对这种“质胜文则野”的结合方式进行过批评。伦理—政治美学讲究的是将审美与道德、政治结合成一个有机体,使得二者能够相互促进从而形成一种更为整全的审美体验。在伦理—政治美学的审美体验中,因为有道德、政治因素的激荡而使得审美更为丰盈、更具浩然之气——儒家美学所讲的“三月不知肉味”、“大”、“荡荡乎”、“风骨”、“气盛言宜”、“孔颜乐处”、“曾点气象”等正是因道德感的渗透而带来的积极审美感受。同时,因为有感性审美因素的传达而使得道德与政治更为形象、更具感染性——儒家美学所讲的“比兴”、“礼仪”、“乐象”、“济济翔翔”、“比类”、“图鉴”“兴象”、“涵泳”等正是因美感形式的承载而带来的自觉道德感发。同样,在伦理—政治美学指导的文艺创作中,因为有道德与政治价值的担当而使得文艺创作更具现实关切性与社会责任感。
作为一种当代美学形态的伦理—政治美学,给审美与道德、政治关系的处理在相一致与相分离模式之外带来了一种新的方案。这种在美善区分基础上又进行美善关联的美学新形态,既回应了现代美学对审美与道德、政治的区分要求,又具有当代美学的关联型特色。运用这种美学形态去回应当代的美育理论问题,也许能带来一些新的理论启示。
三、儒家伦理—政治美学与当代美育理论问题
儒家“美善合一”关系及其当代伦理—政治美学理论形态的建立,带来一种对“美”、“美学”范式理解的新视角。在儒家“美善关系”与伦理—政治美学中,“美”不再单指形式之美以及因这种形式在人心理产生的情感愉悦,而是指形式与内容、情感与理性内在结合之“大美”以及由此在人生命体验中产生的美善、情理相融感。作为一种可供选择的当代美学形态,伦理—政治美学虽然不能解释所有的审美活动,但其对以完善人格为目标的审美教育活动却具有极强的阐释力。《性自命出》云:“教,所以生德于中者也。”作为一个高度重视人文教化的文明古国,中国儒家美学思想的提出本身就是针对如何教育人的问题而提出的。中国现代美学学科的建立,其意图也在于要通过审美教育来改造国民性,培养新人格。这就表明,儒家美学与美育理论之间有着天然的亲和力。在“美善合一”的伦理—政治美学框架下,当代审美教育的性质与地位问题能得到一种更合理的解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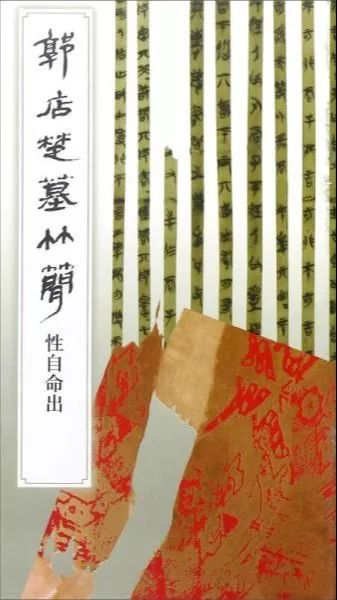
先看审美教育的性质问题。审美教育的目标在于完善人格,这是公论。但是,审美教育相比其他教育,在完善人格方面有什么不同之处呢?这实际涉及到审美教育的性质问题。在现代区分型美学观念中,美——情感——反思判断力与善——意志——理性是分属不同领域的。在这种现代美学观念影响下,学界在定位审美教育的性质时,往往更为关注去凸显审美教育不同于道德教育的独特性所在。可以说,美育是情感教育、美育是趣味教育、美育是感性教育、美育是艺术教育、美育是美学知识教育等主张都是一种寻找美育独立性之运思。[13]这些主张虽然都合理地看到了审美教育的独特性所在,但其间始终有一个难题无法解决,即审美与道德人格的正向对接问题。不可否认,在现代美学框架下,一个人审美素养的提升可能也会提升他对人生其他方面的洞见,进而对人生如何在世有更高的感受与领悟。但需要指出的是,在现代性美善分离的美学框架下来谈“以美激善”只能是一种或然性推理而非必然性结论。一个人的情感、趣味、感性、艺术感知力与技艺、美学知识固然是一个完善人格应当具有的,但在“非功利性”的美育思想指导下,这种审美能力的提升或审美单向度人格的完善并不必然生发人格全面完善之效果。由于真切性地表现一种精神境界与艺术性地描述一种精神境界是不同的,故为人与为文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正向关联。“修辞立其诚。”中国传统美学所说的“文如其人”,其预设的理论前提在于文章确实是个人内在精神真诚的体现,否则就会出现虚情假意,假人假文。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之六)有云:“心声心画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14]潘岳、赵孟頫、董其昌等人的审美素质不能说不高,但其审美与道德、政治水准之间的错位也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上确实存在这种情况:通过审美教育,一个人的情感丰富了、趣味增强了、感知能力敏锐了、艺术技能提升了、美学知识渊博了,但道德或政治人格却并未得到提升甚至还变得低下了。认为通过这种价值独立性的审美教育必然带来情理中和、身心协调与人格完满,这只是一种“审美乌托邦”式的臆想。杜卫就说:“当美育被仅仅限于对审美‘无利害性’的应用时,美育的意义就变得稀薄,美育的价值和功能就被狭隘化、抽象化了。这种狭隘的美育‘自律论’与粗暴的美育‘工具论’一样,都不能全面把握美育的性质和功能,对于美育的实践也会是有害的。”[15]这种审美教育与道德、政治人格的疏离实际是美善区分型美学形态必然带来的一种结果。要解决这一矛盾,只能是对情感、趣味、感性、艺术、美学知识等审美性内涵予以一种正向道德与政治价值的引领与激发。但如此一来,这种补救措施又与其凸显审美教育“无利害”之独特性的理论初衷相违背。这一悖论正如刘成纪说的:“自康德以来,美学领域固守的审美无利害或者超功利原则却是从根本上排斥美育的。这是因为,任何教育都是有目的的,都带有无法去除的外在强制色彩。就此而言,谈审美就不应该谈教育,或者说一涉及‘教育’,就在根本上背离了美超越功利的自由旨趣。”[16]
然而,在“美善合一”的伦理—政治美学理论框架下,这一悖论根本不存在,因为其审美能力的提升与道德、政治人格的完善本身就是正向对接的。伦理—政治美学参照下的审美教育,本身就是有道德与政治反思性的情感教育、趣味教育、感性教育、艺术教育与美学知识教育,其既注重了情感、趣味、感性、艺术、美学知识等层面的培养,又给这种培养予以了正面的方向性引领。相比于当前存在的对美的多元性理解,伦理—政治美学所讲的有道德与政治内容的“美”,本身算是一种狭义的美。但正是这种狭义的美也使得审美教育剔除了可能引发的反向人格之教育效果,而使得审美教育的性质与完善人格直接对接。不仅如此,伦理—政治美学所蕴含的政治性内涵还有利于扩展当前的将美育性质更多定位于个体修身层面的理论致思。个体感性的培养、情感体验的丰富与道德水准的提升固然是美育的题中之重,但完善的人格除了个体素质自身的完善外,还应包含着个体对社会进行参与的责任感与行动力。《孟子·尽心下》云:“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儒家伦理—政治美学就是在个体修身之美的基础上,提倡一种以己推他,成己成物,进而化育天下的人格扩充。《乐记·乐本》云:“声音之道,与政通矣。”儒家的礼乐文化也是强调在个体之仁的情感体验下,扩充为对他人的爱,进而拓展为对国家政治的认同情感,最后升华为一种“与天地同和”、“与天地同节”的境界。这种将个体情感与政治认同乃至天下认同相关联的理论实给美学与美育的发展打开了广阔的社会实践空间。伦理—政治美学视野下的美育,既不是将美育与社会政治实践完全分隔,也不是要将美育与社会政治实践混同,而是将社会政治维度内化在美育当中,这无疑为培育与提升公民的政治人格提供了一个重要窗口,将大大增强美育的社会实践功能。
再看审美教育的地位问题。审美教育的地位问题主要涉及到的是美育与德育地位论争的问题。目前对德育与美育关系的探讨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是将美育视为德育的一部分,或将美育看作是德育实施的手段。二是认为美育与德育是有区别的,美育与德育具有同等地位。第一种看法将美育仅当作德育的教育形式,显然既不能得到现代区分型美学理论的赞同(因为没有将美育独立出来)也得不到伦理—政治美学的支持(因为是一种“美善关系”的外在目的论)。第二种看法是当前的主流看法。正是看到了审美教育在促进人格完善方面有着道德教育不同之处,故从王国维的“始于美育,终于美育”、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梁启超的“趣味教育”、朱光潜的“人生的艺术化”等提议开始,中国的有识之士都在强调审美教育的重要性。虽然当前审美教育已经受到了国家、社会与个人的重视,但依然有进一步推进的空间。随着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审美教育应成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推进器。在伦理—政治美学视域中,审美教育的需要当能更好地成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必要组成部分。伦理—政治美学将道德与政治价值内置于审美中,使得美育本身就包含了德育部分的社会功能。虽然美育无法完全取代德育,但相比将美育与德育并置的主流看法,这种美育观念显示了美育比德育具有更大的重要性。美育不但在满足人对“美”的生活需要,同时也在满足人对“好”的生活需要。这就表明,以伦理—政治美学为参照,适应新时代主要矛盾的转化,审美教育不但不是德育的一部分,而且也不是与德育具同等地位,而是在某种程度上要高于德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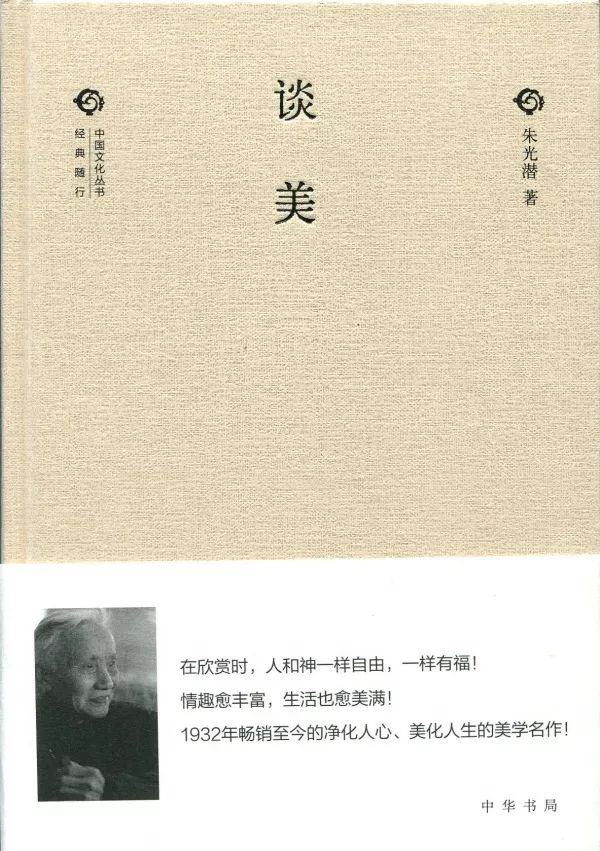
事实上,随着图像时代、体验经济时代、微时代、日常生活审美化时代的到来,美开始成为人们感知世界的重要方式。“进入微时代,随着美的知识边界被沟通无限的移动互联网信息生产与消费能力所破坏,微时代生活赋予人的日常感受以更加广泛而直接的审美生动性。”[17]由此,科学技术、学术思想、生活知识、道德政治价值观念等都开始借助美的方式来进行信息传播,而大众也更多地是通过审美的生动性来感知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也成为新时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方法。可以说,生活的审美化与感知世界的审美化为当前美育地位的重要性提供了强大的时代背景。拿德育来说,抽象、灌输性的道德规范性教育远远不能满足当代的需要,实有向美育借鉴或向美育转型的必要。儒家美学一直就强调美育相对于德育在教育效果上的优越性。《性自命出》云:“凡声,其出于情也信,然后其入拨人之心也厚。”《孟子·尽心上》云:“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荀子·乐论》亦说:“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黑格尔说:“音乐凭声音的运动直接渗透到一切心灵运动的内在的发源地。”[18]相比于德育的抽象规范性,美育以自身的感性形式与情感感染力即切近了人之情性,又符合了时代无处不在的影像环境,因而能在与生命感性、情感相应和的美感熏陶下,在触目皆是的影像之流中来自觉完成人格教化,实现人的感性与理性的完善统一。这是一种在生动形象、兴趣盎然的气氛中与俯拾即是的社会影像环境中实现对生命潜移默化的人格教化,其教育形式是便利的、全民性的,其教育效果也是轻松的、自觉的、深刻的、高效的。由此可见,伦理—政治美学视域下的审美教育,不但承载了德育的部分功能,而且本身还具有远比德育更为优越的教育效果、教育环境与更为整全的教育内容,其重要性自当要超过道德教育。这将迎来美育地位的再次提升!
综之,儒家“美善合一”并依此原则建构的当代伦理—政治美学形态,改变了现代美学体系带来的诸多应用美学问题,能为当代审美教育理论提供良好的理论基础。由此,如何去完成美学学科由现代区分型向当代关联型的转换、如何重新去界定“美”的理论内涵、如何去重建美育学科的哲学美学范式,当是一个摆在美学界同仁面前的迫切理论问题。
参考文献:
[1]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编:《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9页。
[2]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67页。
[3]关于对孔子《论语》中“美”字的语义更详细的分析,可参看拙文《孔子论“美”及相关美学问题的澄清》,《孔子研究》2012年第5期。
[4]〔意〕克罗齐:《美学原理/美学纲要》,朱光潜等译,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13页。
[5]周锡山编校:《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5页。
[6]关于用实用理论来评价孔子文学理论,可参看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在其他诸多的中国美学史和中国文学理论史中这种观点依然还在盛行。
[7]〔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90页。
[8]〔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46页。
[9]朱光潜:《文艺心理学》,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
[10]张法:《从世界美学的两大类型看美学的当下演进》,《学术月刊》2015年第4期。
[11]可参看J.Levinson主编的《美学与伦理学》(Aesthetics and ethics,1998)、J.L.Bermudez和S.Gardner主编的《艺术与道德》(Art and Morality,2003)、Elizabeth Schellekens的《美学与道德》(Aesthetics and Morality,2008)等著作。
[12]〔德〕沃尔夫冈•韦尔施:《重构美学》,陆扬、张岩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79-80页。
[13]学界对美育性质的相关理解,可参看叶朗:《美学原理》第十四章,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4]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449页。
[15]杜卫:《论美育的内在德育功能》,《社会科学辑刊》2018年第6期。
[16]刘成纪:《审美教育:现实问题与变革之路》,《中国美术报》2017年9月11日。
[17]王德胜:《微时代:生活审美化与美学的重构》,《光明日报》2015年4月29日。
[18]〔德〕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上),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49页。
原文见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03期
基金:中国人民大学 2019 年度“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 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
作者简介
余开亮,男,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美学教研室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典美学,主要著作有《六朝园林美学》、《艺术哲学导论》、《先秦儒道心性论美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