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荐丨谢地坤译:《判断力批判》
日期:2025-10-15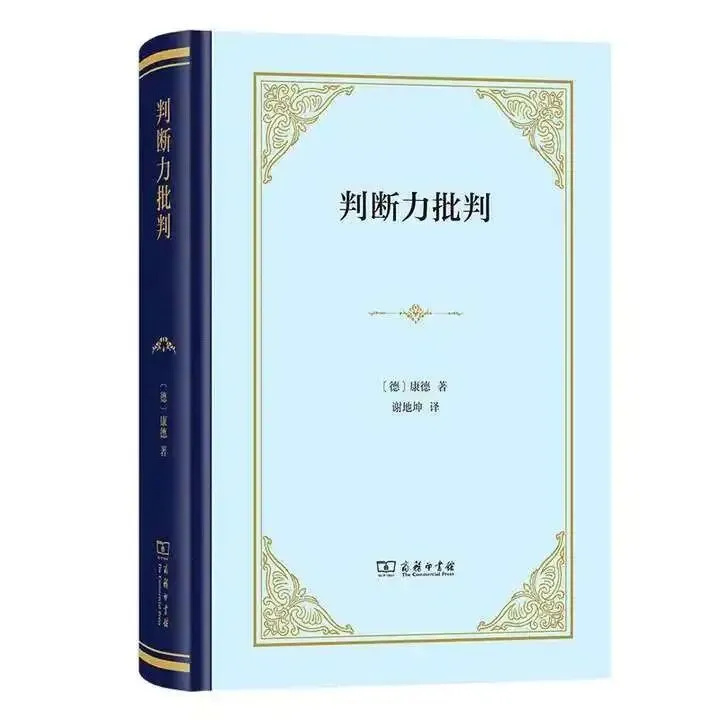
作者简介

谢地坤,江苏南京人,哲学博士。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高级讲席教授。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专家,全国科技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哲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学术期刊审核专家,《东西方哲学年鉴》(中、英文版)中方主编,大百科全书哲学卷第三版执行主编。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所长,《哲学研究》、《哲学动态》、《中国哲学年鉴》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系主任,博导。主要研究方向为欧洲大陆哲学,代表性成果有《费希特的宗教哲学》、《走向精神科学之路》、《求真 至善 惟美》、《西方哲学史》(第六、七卷)等。
译后记
《判断力批判》是康德批判哲学体系的最后一部著作,出版于1790年。全书分为“导论”、“审美判断力的批判”和“目的论判断力的批判”三个部分,在后两个部分又分别设有“分析论”和“辩证论”,最后还有一个附录,名为“目的论判断力的方法论”。“导论”讨论哲学领域的划分,重点是讨论判断力如何作为中介将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联结为一个整体。“审美判断力的批判”主要分析美的本质和美与崇高的区别及联系,讨论审美鉴赏遇到的“二律背反”的问题,并提出解决办法。“目的论判断力的批判”阐释把自然归为目的系统的原理,尤其是要说明,为何在解释事物的自然目的的时候,机制原理必须服从于目的论原理,最后过渡到对伦理学神学的合理性的证明,这也是“附录”的主要内容。按照康德自己所说,“我会以本书结束我的全部批判工作。”这就意味着,虽然这部著作主要探讨审美、鉴赏、合目的性等问题,但又绝不局限于此,而是与《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一道构成康德的全部批判哲学事业的哲学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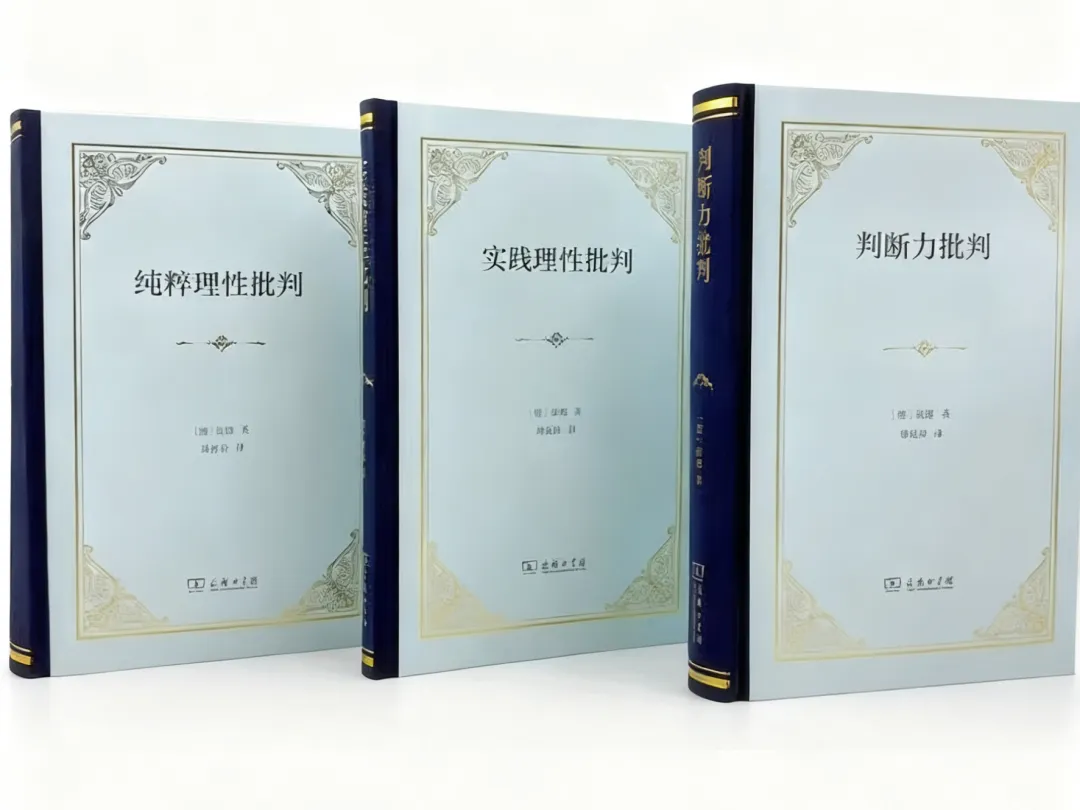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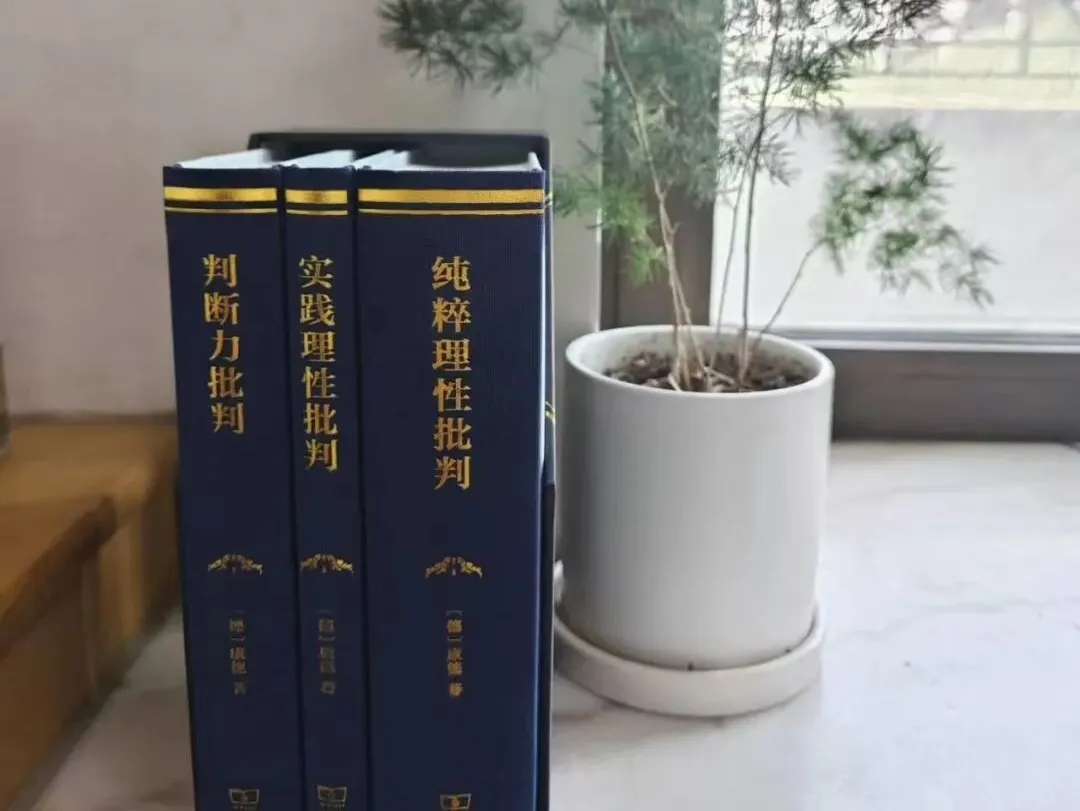
康德三大批判
早在上世纪初康德哲学传入我国时,《判断力批判》就已经引起我国学界的注意。1964年商务印书馆首先出版了由宗白华和韦卓民两位先生翻译的汉译本,此后数十年间又有其他几个汉译本出版,它们都对学界研究康德哲学提供了很好的原著资源。本译本是这部著作的最新汉语译本,为学界又增加了一个新的选择。现将译者翻译本书的体会、汉译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及其解决,以及版本的选择等方面做个简单的说明。
壹
康德始终认为,哲学分为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两个部分。前者是根据自然的先天原理使理论知识成为可能,而后者则是根据自由意志的规定使实践哲学成为可能。这样,哲学就划分为两个领域,即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康德看得很清楚,“这两个不同的领域虽然在其立法方面并不互相限制,但在感性世界里的作用上却是不停地互相限制的,并不构成一个统一体,其原因就在于,自然概念虽然在直观中有其对象,但并不是将其表象为自在之物,而是将其表象为单纯的现象,与之相反,自由概念虽然也把自在之物本身作为其客体,但并不是在直观中去表象它,因此,这两种概念在其客体中都不能获得关于作为自在之物的(甚至是关于正在思维着的主体的)理论知识,这样的客体是超感性的,虽然人们为此不得不为解释所有经验对象的可能性配备理念,但这个理念本身却永远不可能上升和扩展为一门知识。”这样,康德哲学体系的内在矛盾跃然纸上,明显可见。
稍做分析就可以发现,在理论哲学部分占据支配地位的是自然概念,它遵守的是因果性的必然法则,而在实践哲学部分起主导作用的是自由概念,它突出强调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源于自由意志的道德选择。由于这两个部分研究对象不同,它们所遵守的也是不同的原理。这样,在这两个部分中必定会出现不能直接沟通的鸿沟。如果说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自然概念和自由概念可以没有矛盾地共存于同一个主体之中,但自然必然性和自由毕竟是作为二律背反存在着,“它们毕竟在感性世界里的效果中不停地相互牵制,不能构成一体”。而在《实践理性批判》中,“自由概念应当使通过它的规律所提出的目的在感性世界中成为现实”,如果根本不存在这种影响的感性痕迹,那么,受自然法则制约的人永远也无法意识到自己所拥有的自由权利和必须遵守的道德法则,从而使得对超验世界的设想变成毫无根据的。因此,应该有一种从自然人向自由人过渡的桥梁,它根据自然人切身感受到的某种特殊情感,促进人们内心对道德情感的感受性,并且可以向人们显示出超验的道德世界的法则。康德在撰写前两个批判时并未想到自己哲学体系中存在的这个鸿沟,在经过长久的思考之后,不仅发现了这个矛盾,而且还想好了解决办法。这就是1787年他明确认识到,人的鉴赏能力不仅在实践范围中具有自己的作用,而且在先验哲学里也有其自身独特的先天原理,而鉴赏判断只是审美的一部分,更重要的,它无非是以一个对象的合目的性的形式为根据。所以,通过对审美和目的论的分析和批判,就可以使判断力承担沟通这两个领域的重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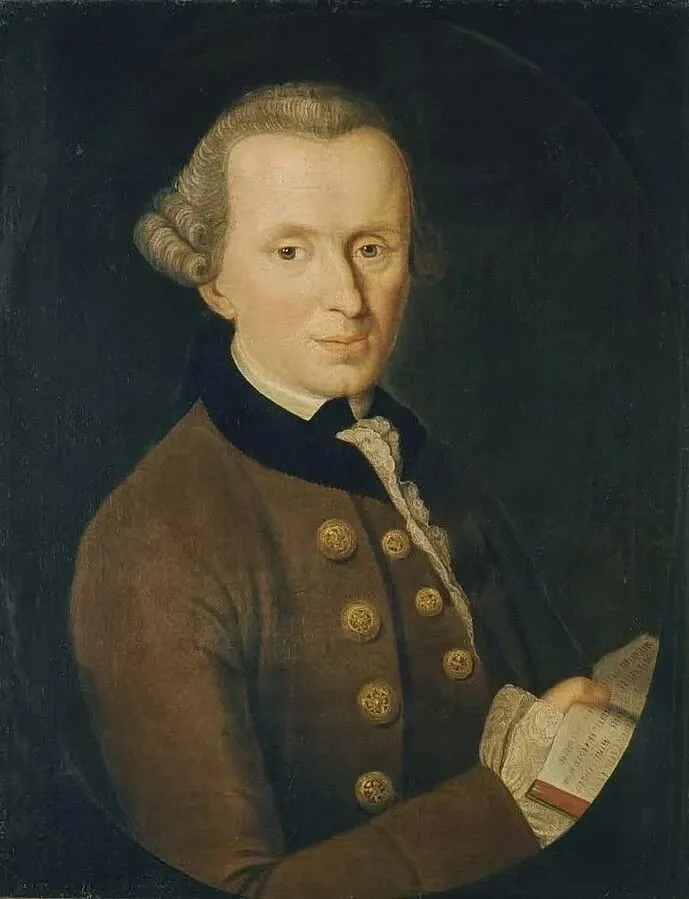
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
康德之所以认为判断力可以沟通以自然概念为主导的自然领域和以自由概念为奠基的实践领域,就在于他相信,人既是自然人,必定要服从自然法则,同时人又是理性的人,具有自由意志,能够进行自我选择,人的这种双重身份使得自由意志及其发挥的作用一定会对自然界发生影响,也就是说,人在使自由概念提出的法则及其目的在感性世界中变成现实的同时,它一方面在改变人自己,另一方面还会让人们必定这样来设想自然界,“即自然形式的合法性按照自由法则至少是与在自然中推进目的的可能性相一致的。”这样, 对康德来说,知性与理性之间的这个中介环节必定只有判断力才能承担,即使它没有自己的立法范围,但它依然可以在自身中包含着一个依据法则去寻求属于它自己的原理。就判断力本身而言,它或许是一个单纯主观的原理,并不能像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那样拥有自己独立的范围,但它毕竟是以人的活动作为其地基,而人的活动离不开感性世界,所以,即便判断力的独特原理都是来自主体的所想所言,在哲学中都必须算作理论部分,但是,主体的一切活动及其效用都发生在感性世界里,其做出的判断也必须在感性世界中发挥作用。所以,判断力的一个典型特征,就在于它自身并不形成一个特殊的部分,而是介于理论和实践之间,在必要时可以随机附加于这两方中的任何一方。同时因为它是人的诸认识能力的自由而合目的性的运用,它一方面来源于人的认识能力,与人的认识相关;另一方面又指向人的自由和道德,与人的实践相关。这样,判断力就可以利用其独特的居间地位,并且以此去消除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阻隔,使自然界的必然法则和人的自由意志统一起来。进一步说,只有判断力才能拥有这种独特的性状和原理,只有判断力的这个原理才会产生这种特殊的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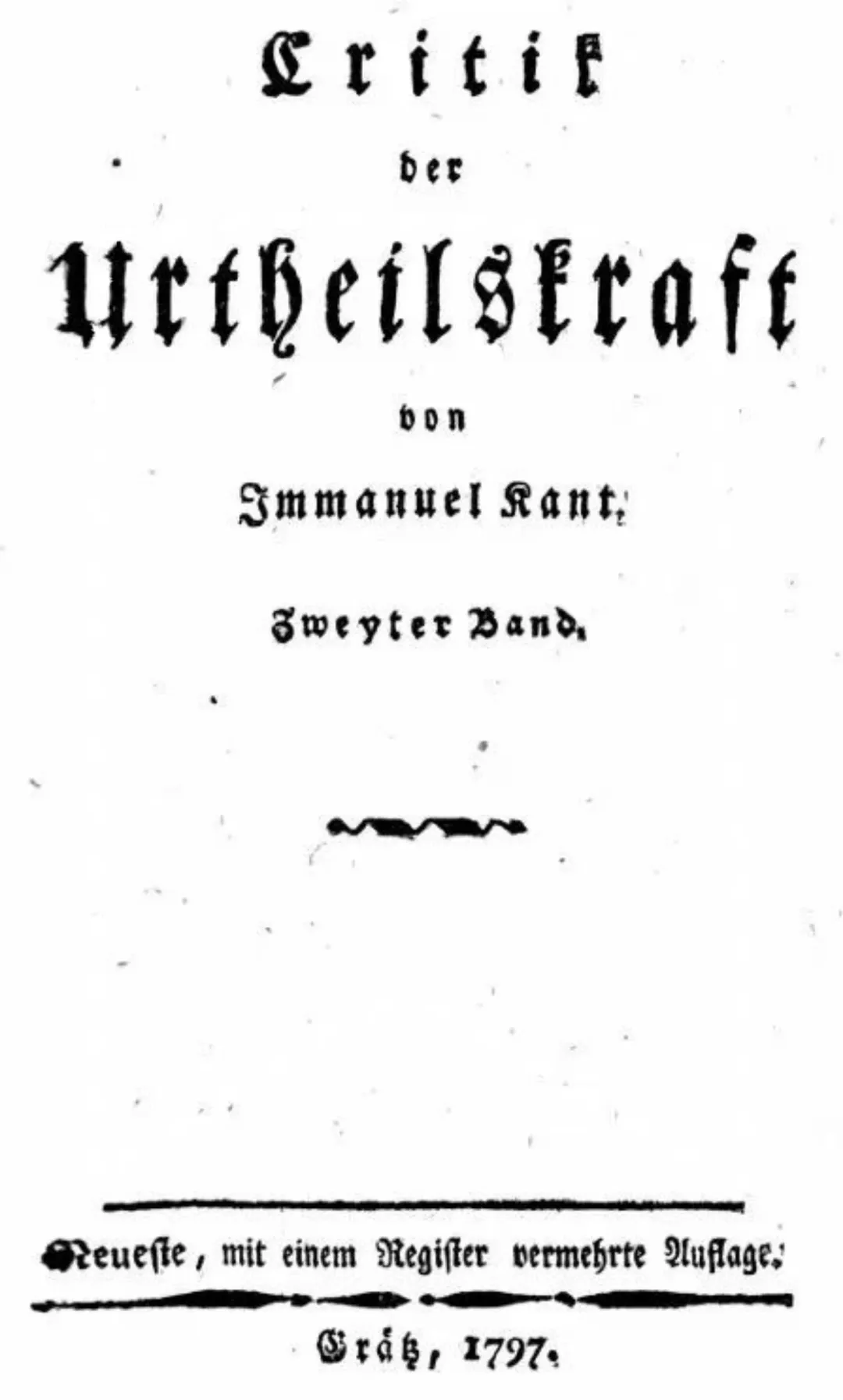
《判断力批判》(Critik der Urteilskraft)第二卷
当然,如果只是限于这样的表述,康德对此所表达的论断就过于简单了。他对此继续解释说,自然只是作为现象才被我们所认识,但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设想自然有一个超感性的基底。我们可以借助判断力所具有的原理,按照自然的特殊规律,为自然的超感性的基底做出由我们理智能力所能做出的可规定性。正是在这里, 康德在强调“判断力就使得从自然领域向自由领域的过渡成为可能”的同时,还为目的论证明和道德神学做了精心的铺垫。
具体地讲,康德在这里走出了关键一步,这就是他将判断力区分为反思性判断力和规定性判断力。康德明确说,一般判断力就是将特殊包含在普遍之中的思维能力。如果普遍的规定、原理、法则等是业已给予的,那么,将特殊归于普遍之下的判断力就是规定性的。反过来说,如果只是特殊是给定的,判断力为此就应当找到普遍,这样,判断力就是单纯反思性的。正是这一区分让人们看到了,判断力只是主体在思考中拥有一个对自然可能性的先天原理,判断力并不是为自然立法,而是人给自己做出法则规定。通过这种将反思性判断力与规定性判断力予以分殊的做法,康德表明了判断力并不是想要先天地认识自然法则,而是为了我们能够认识自然秩序,假定将自然法则从普遍的法则中划分出来。这样做,一方面将人还原到自然之中,人有七情六欲,只是自然界的普通一员,服从于自然法则;另一方面,判断力是人为自己立法,使人终将认识到人的自由必定要与人的认识能力协调一致起来。由此,人自身的活动就要体现在由人自我假定的终极目的之中,并且进而体现在与自然的合目的性的契合之中。所以,反思判断力是打开自然概念与自由概念之阻隔的关键,也是把自然的合目的性与人类理性的目的统一起来的关键,因为它们原来就本为一体,不分为二。
康德由此理直气壮地宣布:“哲学由这三个部分所构成:纯粹知性批判,纯粹判断力批判和纯粹理性批判,它们之所以被称作纯粹的能力,是因为它们都是先天立法的。”康德这种将自然与自由分开后再予以统一,突出判断力在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之间的地位和作用的创举,不仅对他自己完成批判哲学的体系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对后来的谢林的同一哲学和黑格尔的对立统一的辩证法也产生了重要的启迪意义。
贰
《判断力批判》与前两个批判的显著不同,就是重视人的情感的研究,并且将它与美学的建构和伦理神学的讨论结合在一起,这点恰恰构成这个批判的一个鲜明特征。
康德在这里明确说,“把判断力批判分为审美判断力的批判和目的论判断力的批判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前一种批判被理解为通过快乐和不快的情感去判断形式的合目的性(一般也称作主观的合目的性)的能力,后一种批判被理解为通过知性和理性去判断(客观的)自然的实在合目的性的能力。”这就告诉明确人们,审美研究对象的核心是人的情感,分析情感是这个批判所要完成的首要任务,然后才能由此去讨论合目的性。康德并没有像欧洲当时一些思想家那样,将情感的分析陷于单纯的心里描述或心里分析之中,而是将情感与人的认识能力和欲望等分离开来。这样,康德一方面承认,优美吸引人,崇高感动人,所以,通过快乐去做判断的能力就叫做鉴赏,而且这点还是普遍有效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审美判断力涉及判断对象的某种形式,这种形式因为与人们的某些心理功能相符合,从而使人们在主观感情上感到某种合目的性的愉快。但另一方面,康德则强调,审美鉴赏所带来的快乐是一种无利益、无兴趣、无意图的愉悦,所以,审美没有、也不浮现出任何确定的目的(概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康德才说,单纯的审美鉴赏没有刻意的原理,而只是对于愉悦的单纯享受。
于是,这里就带来这个问题:这种基于个人感受的审美如何具有普遍性?

《Hidden Beauty》(Cheryl St.John)
康德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分为几个方面。首先,他在这里借用了在《纯粹理性批判》里的先天综合判断的思想方式,指出每一个主体把一个对象评判为美,不只是说美是这个这个对象的一个属性,更多的是指主体把自己的愉悦感受附加给这个对象身上,所以,这里是主观之想象与客观之表象的一种结合,综合判断在这里发挥主导作用。其次,审美判断不同于逻辑判断,它根本不需要概念,不是去发现事物的客观规律,审美的目的在于追求纯洁的美感,所以,美学不是一门科学。但是,审美不仅具有“质”的契机,而且还要求有“量”的契机,即“美是那种无须概念而能普遍引起愉快的感受”,这种“量”的契机就是人类具有审美的共通感,它使人对美的感受有一种普遍传导性,而不是局限在某些个体那里。这就是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康德由此强调,“从经验来看,美只在社会里让人产生兴趣。”再次,审美的共通感使人们意识到,快乐不只是个体的感性直观,而且还需要反思的基础,即是说,快乐建立在反思契合于一般客体表象的普遍、却又单纯主观的条件之上。对反思来说,客体的形式就是合目的性。这样,康德就把单纯的审美与合目的性结合起来,他直截了当地说,“只有其表象直接与快乐的情感结合在一起,这样的对象才能被称为合目的性的;而这种表象本身是一种合目的性的审美表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审美才具有一种“无目的的目的性”,或者也可以称为“形式的合目的性”或“主观合目的性”。
康德承认,在一个鉴赏判断里出现这种审美判断的普遍性之规定,是先验哲学家值得关注的事情。这是因为,审美判断虽然具有明显的个人主观色彩,但它的这种“无目的的目的性”同时还具有范导性的意义,即使它并不发挥规范性的作用,但它以其追求的“理念”而对其他人的思想和行为发生指导、调节的作用。进一步讲,单纯的审美和崇高虽然都是以感性形式呈现出来的,它们不可能达到与理性的理念完全的契合,“但它们正是通过这种允许感性呈现出来的非契合性而变得生气勃勃,并且由此被召唤到内心里面”。人的内心因为这种奠基于反思基础之上的审美情感和自我提升的崇高情感才会离开感性,离开单纯的自然的合目的性,而是努力去追求和实现那包含着更高的合目的性的理念。
这样,康德通过对人所追求的美的理念与合目的性的对比,强调只有在人的形象这里才可以期望获得美的理想。这是因为,“在人的形象这里,这个理想就存在于德性的表达之中,没有德性,这个对象就不是普遍的,并且也不会因此而积极地使人开兴(而不只是被动地存在于一个中规中矩的表现中)。”在这种不知不觉的推论中,康德已经放弃了前面所说的“审美是无利益、无兴趣、无意图的愉悦”的说法,而是把审美与德行这两个人们在经验世界里经常遇到的实践行为联系在一起。康德当然很清楚,这两者是不同的,前者是出自自由意志,而后者则必须服从于客观的社会规律。而且,人作为自然界的生物,当然要服从自然法则,这是人之为人的自然属性;但人同时还具有自由意志,更是要把人自己所设定的终极目的当作自己矢志不渝、终身追求的目标,这是人之为人的理性使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康德才说出了这番非常有名的话:“美是道德之善的象征,而且只有在这种考虑方面(一种对每个人来说都是自然的关系,也是要求每个人对他人承担义务的关系),它才能够因为要求得到所有其他人的同意才使人感到愉悦,在这种情况下,心灵同时意识到某种崇高和对仅仅接受从感官印象中获得快乐的超越,而其他价值也会根据他们的判断力的类似准则而受到尊重。”
我们由此看的很清楚,康德在这部著作里讨论的虽然是愉悦、美感、艺术、崇高、想象力等问题,但实则都是基于主体的内部的思想活动,而且在方法论上并没有离开他的先天综合判断的思维范式,所以,这部著作说到底还是他的批判哲学体系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或者说是“美的哲学”。
叁
本书翻译采用雷克拉姆出版社1878年版《判断力批判:1790年第一版,并附1793年第二版与1799年第三版全部异文》(Kritik der Urtheilskritik:Text der Ausgabe1790(A)mit Beifuegung saemtlicher Abweichungen der Ausgabe 1793(B)und 1799(C),herausgegeben von Karl Kehrbach,Verlag von Phillip Reclam Jun.,1878)为底本。在翻译的过程中,本书还参考了以下版本:1.德国汉堡的迈纳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德文本《Die Kritik der Urteilskraft》(Die Kritik der Urteilskraft,Felix Meiner Verlag, Hamburg 2009);2.德国科学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康德文集-第八卷》(Immanuel Kant:Werke, in zhen Bänden,Wissenschaftliche Gesellschaft, Bd.8, Darmstadt,1983);3.剑桥版英译(Critique of the Power of Judgment,translated by Paul Guyer and Eric Matthew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
有关诸版本的文本差异,本书仅选取对中文读者有益的内容差异进行说明,而省略单纯拼写和语法修正。此外,国内已经出版的几个汉译本,对译者的翻译都有启发,借此机会,也向这几位译者表示真诚的感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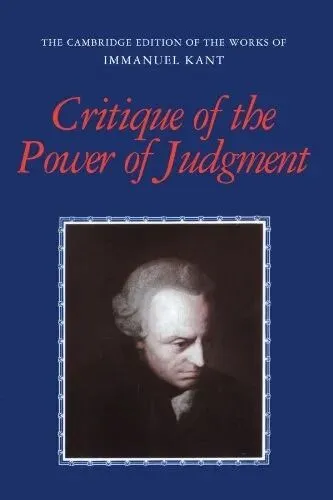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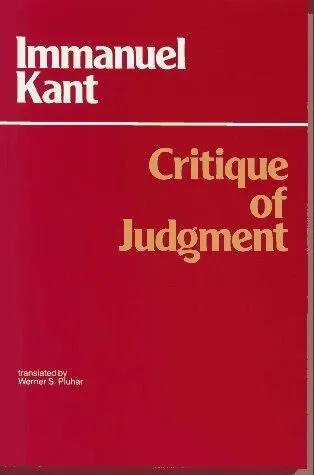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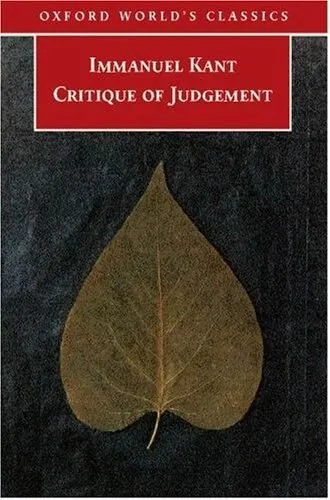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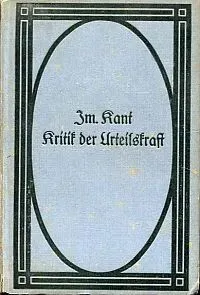
康德三大批判《判断力批判》的部分版本
需要说明的是,康德在撰写《判断力批判》过程中曾经写过一个“导言初稿”。但在完成全稿以后,康德对这个“初稿”不满意,认为它篇幅过长,而且内容不清楚,即使对它删减压缩也不会做出实质性的改变。于是康德在1790年1月至3月间重写了“导言”,也就是现在读者看到的1790年正式出版时的这篇“导言“。但是,1793年康德将当初撰写的“导言初稿”寄给自己早年的学生J.S.贝克,并且写信说,最初所写的导论初稿并不是可有可无,毫无意义的东西,它对诠释批判哲学、尤其是论证自然的合目的性是具有一定价值的。
贝克很好地保存了这篇初稿,并且在不少报刊上发表了其中的一些章节,还发表了他自己撰写的一些评论。1793年由卡西尔负责的普鲁士科学院版《康德著作集》完整地出版了这篇“导言初稿”,引起了哲学史家的普遍关注。(关于“导言初稿”的撰写和出版过程,请参阅德国汉堡迈纳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Die Kritik der Urteilskraft》中第475—478页的说明。)此后随着康德研究的深入,关于这方面的追踪研究和报道也是层出不穷,其原因就在于它对于人们理解和研究《判断力批判》很有裨益。这就是我们在这里将其全文翻译、并且刊登于此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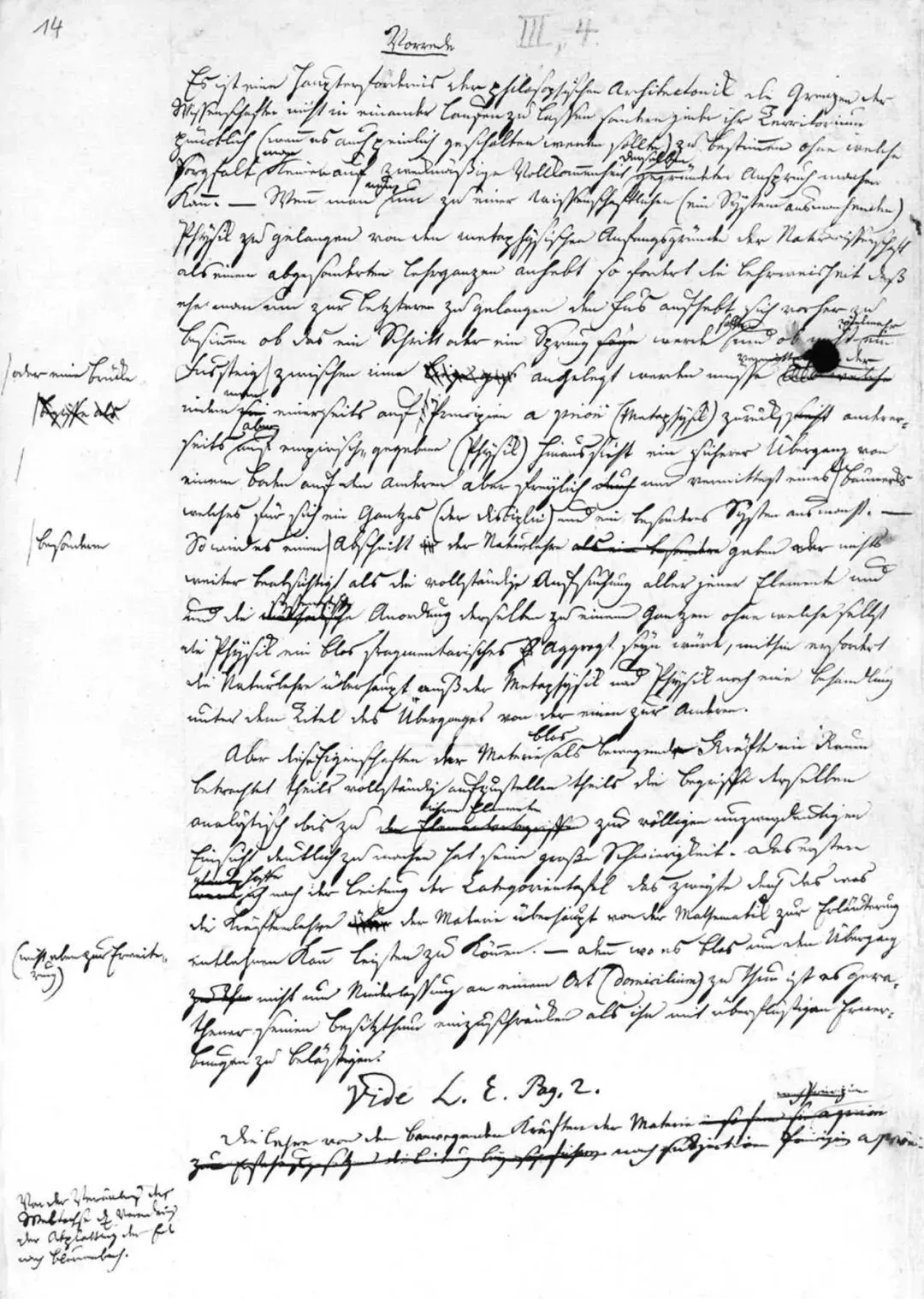
康德手稿
对此还需要说明的,就是为什么我在这里将“Die erste Einleitung in die Kritik der Urteilskraft ”不译为“第一导论”或“第一版导论”,而是译为“导言初稿”或“导论初稿”。其理据如下:其一,若是译为“第一导论”或“第一版导论”,在逻辑上就应该有“第二导论”,但事实是康德对这个最初稿子弃之不用的,康德生前从未将这个稿子用于《判断力批判》的导言,也从未说后来的“导言“是第二导论;其二,既然不存在所谓“第一”“第二“,那就是如何理解“Die erste Einleitung in die Kritik der Urteilskraft ”中的“erst”的问题了。在西文中,无论是德语的”erst“ ,还是英语的”first”,除了”第一“的意思之外,还有”最初的“、”起始的“等意思,所以,要是完全直译,译为”判断力批判的最初导论“或许更为妥帖一些。其三,在迄今出版的德语《判断力批判》中,有些版本就用”“Die erste Fassung der Einleitung in die Kritik der Urteilskritik”的表达,表达了这是第三批判最初导言的意思,其用意就是担心这里出现歧义,防止读者对此发生误解。据此,我以为将此标题翻译为”判断力批判导言初稿“更符合原意,也符合现代汉语的表达习惯。
当然,这里还要说明,这部书里有大量康德哲学所特有的概念、术语等,为遵守翻译界所倡导的“约定俗成”的原则,更为方便读者的阅读,我一般都保留现在通行的译法。但是,下列一些概念和名词的翻译是必须作出解释的。
1.“Ästhetik”在德文中的原义是“感性”,自从德国哲学家鲍姆加登将它专门用于美的分析,这个词常常也有“审美”、“美学”等意思。国内学界通常在翻译康德的《纯粹理性批评》时将它译为“感性”,而在翻译《判断力批判》时则将它译为“审美”或“美学”。但需要注意的是,康德在第一批判中已经明确表示不同意鲍姆加登的用法,指出源自于经验的美的分析不可能上升为理性原则之下的美的批判。在第三批判中,康德强调作为鉴赏判断的感性判断既与美相关,也与崇高相关。由此可见,“感性判断”是一个上位概念,包含着审美判断和崇高判断两个部分。但是,康德本人对此的解释也是不自洽的,在本书开篇讨论美的第一契机时明确说,“鉴赏就是判断美的能力”。这就给翻译这个概念带来很大困难,无论用“审美”,还是用“感性”来翻译“Ästhetik”似乎都不完全与康德所要表达的意思完全切合。译者在本书中虽然还是沿用约定俗成的“审美”、“美学”,但也包含“感性”的意义。
2.“Mechanik”是在第三批判里不断出现的一个关键概念。这个词一般是指机械装置、机械驱动、机械操纵等,因此,哲学界通常都把这个词翻译为“机械论”、“力学”等。但是,康德在这里是用这个概念来表示自然界的万事万物仿佛受到某种目的的驱使、不由自主的生成、发展,乃至最后形成某种自然合目的性的活动,而不是指力学意义上的机械作用。比如,他在评论古人寻找世界发生的原因时就说了这样的话;“如果他们观察自然事物的安排和进程,他们肯定会找到足够的根据,以此去假定某种超越机制的东西是自然事物的原因,并且猜测在这个世界的机制作用后面有某些更高原因的意图,他们只能把这些更高原因想象为超出人类的东西。”显然,这里的“Mechanik”并不是通常所说的“机械论”,因此,我在这里将这个词翻译为“机制”,意在强调这是自然界的一种随机而动、自然而然的活动,以与康德所说的自然的合目的性的意思相契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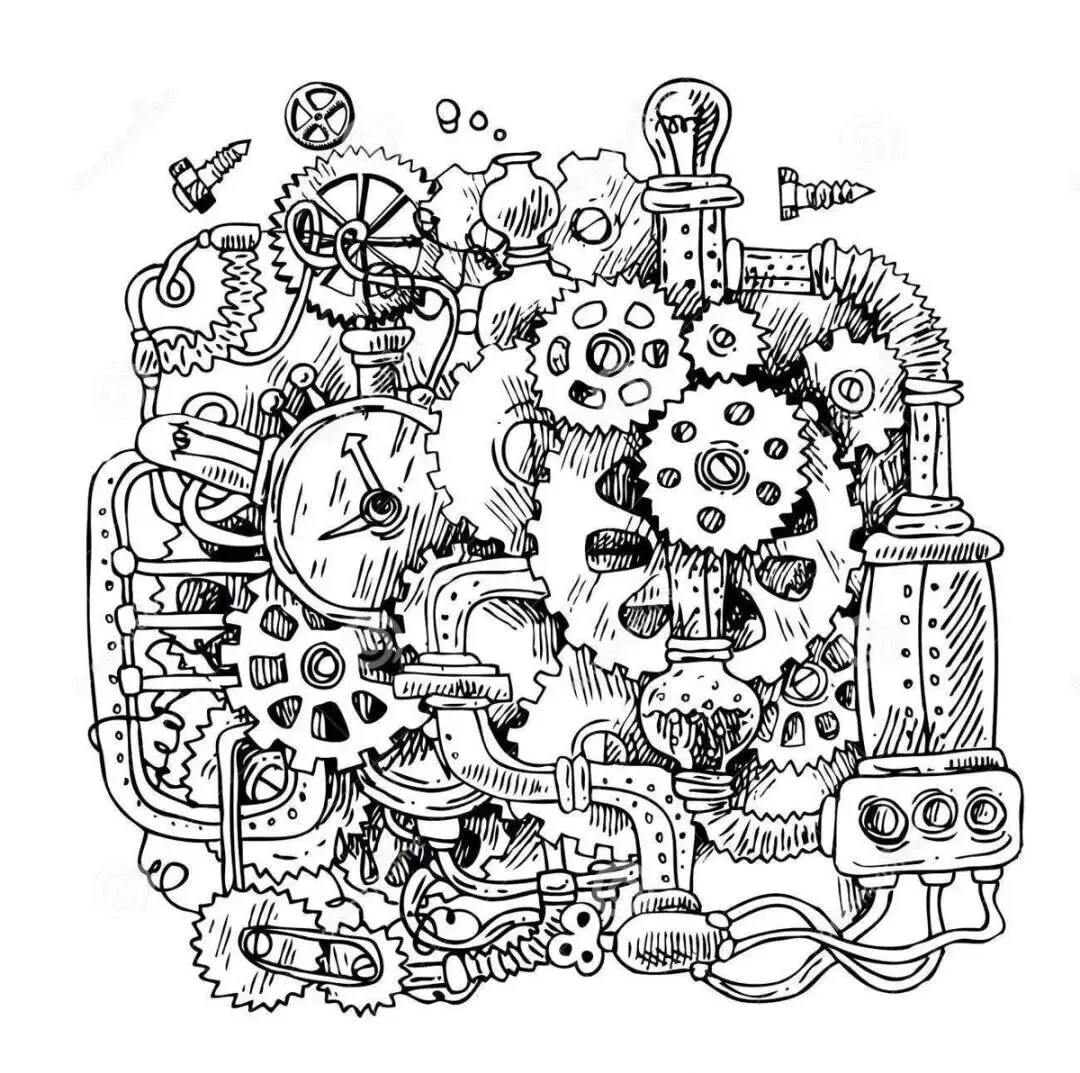
机械装置
3.“Spiel”这个词也是在《判断力批判》里反复出现的一个词。它原本是个多义词,既有“游戏”,“把戏”的意思,也有“表演”、“竞赛”的意味,但它最基本的含义是“动起来”、“活动”。如果我们把这个词统统译为“游戏”,就会出现所谓的“感觉的游戏”、“概念的游戏”、“思想的游戏”、“美的游戏”、“想象力的游戏”等等让人无法理解的说法,而且这些说法又与康德想要表达的思想相去甚远。假如我们看看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几个汉语译本,译者们都是根据上下文的意思来翻译这个概念的,例如在“先验逻辑学”里谈到逻辑规律的命题时,我们通常就翻译为“逻辑规律的运行(Spiel)”;在辨析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的时候,我们就译为“思想活动(Spiel)”。如若不然,就可能造成非常不当、甚至是错误的理解。
4.“Heautonomie”是康德在这里使用的一个非常特殊的概念,他的原意是要将这个概念与“Autonomie”(自律)和“Heteronomie”(他律)区分开来。从希腊文的词根来看,这个词的基本意思是“给自己做出法律规定”,近似于“自律”。而从这里的上下文来看,康德是想用这个概念来表达判断力通过反思给自己做出法律规定,与“自律”又不完全一样。现在几个汉语译本有不同的译法,似乎与康德的原意有些出入。故此,我在这里姑且将它译为“自主律”,以与前面的“自律”的译法对应起来。
5.康德哲学中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概念,即“Verstand”,用作形容词则是“verständig”。这个词原来的意思很简单,就是“理解”,“理智”、“智能”、“智力”等等。但是,由于康德在第一批判中将认识过程分为“感性”、“知性”(Verstand)和“理性”三个阶段,所以,我们一般在翻译德国古典哲学著作中都把这个词翻译为“知性”。但是,在这本书里,康德在谈到“目的论”和“道德神学”的证明时,已经不再是在认识论的角度上应用这个概念,而是还原到本体论意思上所说的人的“才智”和上帝所具有的“智慧”那里。比如,他说,“人们当然有理由抱怨说,我们把所有这些安排都建立在一个伟大的、对我们来说不可估量的理智(Verstand)的基础之上,并让这个理智(Verstand)依据这种意图来安排这个世界,那这有什么帮助呢?”如果我们在这里依然翻译为“知性”,那就很难说是与康德所想表达的意思相一致了。因此,在本书前半部分,我一般将这个概念译为“知性”,而在后半部分讨论合目的性和道德神学时,大多情况下都译为“理智”。
6.在本书中,康德还经常使用一些语词的双关意义。比如,“Interesse”就是个频繁出现的单词。在德语中,“Interesse”既有“利益”、“利害”的含义,也有“兴趣”、“兴致”的意思。从康德在本书中的应用来看,他常常是取用这个词所具有的双关意义,译者只能从上下文来做取舍,但并不敢自诩可以完全契合于原文的含义。与此相似的是“Natur”这个词,既有“自然”、“自然界”的意思,也有“本质”、“本性”的含义,康德也是常用这个词的多重意义。难怪阿多诺说,假如有人愿意,可以专门对康德哲学中的这些双关意义的用法写一篇博士论文。
上述说明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一些体会,希望有助于读者的理解。康德的书本来就不好懂,而《判断力批判》更是难上加难。在翻译的过程中,常有学力不逮、绠短汲深之虞,幸有许多学友的帮助和鼓励,才使我按时完成这本书的翻译。限于译者的学力,译文难免有错漏、不当之处,敬请学界和读者批评指正。
最后,我务必要感谢商务印书馆的陈小文总编。他与我相识相知多年,数年前他就向我提出翻译本书的建议,由于种种原因,我一直没有明确答复。去年6月,我们一道在北京香山饭店开会,他在晚上闲聊时又一次郑重向我提出这个建议,我亦感到此事值得一做,便答应下来。此后,只要见到我,他就会督促我做好这件事。正是在他的激励下,我才能顺利完成这项工作。我还要感谢王艳秀博士,她是我当年的博后,现在是上海师大的副教授。她读书甚广,文字练达,而且还有很好的学术见识。这次我专门约请她审读文稿,她发现了其中一些问题,并提出很好的建议,这对提高文稿的质量大有帮助。最后,我要特别感谢商务印书馆的龚李萱博士,她对照原文认真审读了译稿,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增补了原文各版本差异的脚注。正是她的细致编辑和加工,才使本书能以现在的样式与读者见面。
本书的翻译得到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重大项目“认知中的情感与理性研究”(22JJD720006)的支持,在此译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译稿完成之时,恰逢康德诞辰300周年,谨以此书的翻译缅怀和纪念这位伟大的哲人!
谢地坤
初稿于2024年5月
再稿于2025年2月
转自:文艺复兴与近代哲学 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