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峰:《庄子·养生主》的宏大生命观——从其关键词和结构说起
日期:2024-12-18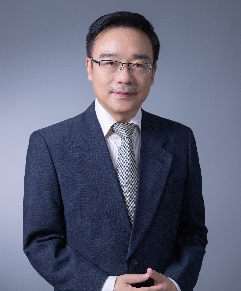
摘要:《养生主》各个部分都是以“天”为中心展开的,养生之“主”亦即要领就在于“天”,只有“依乎天理”,只有“知天”,只有不受人为束缚,只有泰然接受“天之刑”,只有“安时而处顺”,才能获得满意的人生。从结构上看,《养生主》各段落是前后一贯,彼此呼应的。并无旁出的支脉,无关的论述。《养生主》所要养的不仅是有限的肉体的生命,也是包括死亡在内的超越的无限的生命,是能够坦然应对现实人生困境的生命。可以与《养生主》相互启发的文献是内篇的《德充符》《大宗师》和外篇的《山木》。
前言
《养生主》虽然是《庄子》内篇中最短的一篇,但是值得关注的焦点、需要讨论的难点依然很多。在笔者看来,在《养生主》四个寓言中,目前的研究较多集中于第一个寓言“庖丁解牛”。[①]在《养生主》整体思想脉络中,目前的研究较多集中“生”与“知”的紧张关系。[②]这种角度虽然很有启发,但也形成了一定的偏颇。毫无疑问,《养生主》是一篇讨论“养生”的文章[③],但此文体现出一种宏大的养生观,而不是围绕养形、养心、养神、养性展开的有限养生观,其实质是一种包括如何面对死亡在内的宇宙论意义上的生命观,是一种能够坦然应对现实人生困境的生命观。因此《养生主》的关键词与其说是表达有限与无限之关系的“生”和“知”,是表达养生技巧的“缘督”,不如说是表达万物发生之源、存在之理和必然归宿的“天”;《养生主》养的不仅仅是有形的身体,也养的是从容面对复杂社会的生命,养的是泰然面对死亡的超然境界。可以与《养生主》形成对照的最佳参考文献与其说是《达生》,不如说是《德充符》《大宗师》和《山木》。
一 《养生主》的关键词与此篇的结构
在《庄子》流传过程中,《养生主》给人印象最深、或者说最脍炙人口的地方有两处,一是“庖丁解牛”这个寓言,二是开篇“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这段话。
一般认为“庖丁解牛”表达的是一个“技进乎道”的“三部曲”,即庖丁如何从“所见无非全牛”,到“未尝见全牛”,再到“更无牛”的过程。[④]庖丁能够让一把刀用了十九年而如“新发于硎”,关键在于两点,首先他懂得“缘督以为经”的原理,[⑤]从而能够“以无厚入有间”,顺物自然,从容行走于各种阻碍之间,在夹缝之中自由穿行。所以即便《养生主》中没有出现“中”“虚”这样的词汇,也可以说表达的是相关的精神。[⑥]
其次从“知”的角度来讲,这是一个摆脱官能之知的局限,从而使“神”得以“行”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借助技走向道,从小知走向大知的过程。因此,学者一般都会借助《达生》中承蜩老者、操舟者、善游者、削木者等事例,阐述《养生主》中有类似“用志不分,乃凝于神”的描述。[⑦]这样,就容易导致一种倾向,即从工夫论的角度看,认为养生的关键就在于养心或者养神,将“道”与自己的生命合为一体,从而聚精会神,最大程度地摆脱外物的束缚,实现身心的完全自由。
结合“庖丁解牛”中的“官知止而神欲行”,再结合《养生主》开篇“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也有学者认为《养生主》强调的是如何摆脱对于有限之“知”如有生之知、官能之知的追求,而将“知”安顿在“无涯”之中。这样也就可以和《养生主》“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联系起来。即以“不知”为知,从而进入“无涯”、无“尽”的状态。[⑧]
按照以上的理解,《养生主》就是围绕“缘督”的观念和关于“知”的认识展开的,并可以总结为是一种养生的工夫论。然而,《养生主》真的就仅仅是一种工夫论吗?或者仅仅是一种对于“知”的反思吗?我们认为,结合《养生主》整篇来看,仅仅利用“庖丁解牛”和“生”与“知”的关系理解《养生主》是不够的,仅仅将《养生主》理解为是一种工夫论也是不够的。《养生主》虽短,虽然“庖丁解牛”以及“生”“知”关系那段话最亮眼,但仍然需要结合其他的寓言和叙述,从整体上做出考量。
我们认为,《养生主》的关键词是“天”,“天”可以贯穿《养生主》所有的寓言和论述。《养生主》要解答的是人生困境,因此所养的“生”不仅仅是身体,也是社会关系中的生命,也是宇宙大化中的生命,而这几种生命都必须遵循“天”的法则,才能得到妥善的保护和合理的安顿。[⑨]
首先来看“庖丁解牛”中的“天”,“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因其固然”,强调的是认识、遵循“天理”及其“固然”(天生之本然)的重要性。作者虽然没有指出“天理”指的是什么,但结合上下语境,可以说这是一种复杂的结构,其中既有足以让刀锋卷刃的坚硬骨头,也有“大郤”“大窾”这类中空的间隙,这同样可以形容人间的险恶、生存的困境,以及游走其间的可能性。“缘督以为经”就是充分认识和掌握其中的机理,以一种近乎舞蹈的美妙方式(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踩着与“天理”同样的节奏,不与其“固然”相对抗,凭借“以无厚入有间”的技巧,最终达致“游刃必有馀地”的境地。毋庸置疑,这里的“刀”比喻的是行走于世间的身体,要想不因自己的无知和莽撞而遍体鳞伤,中道早夭,唯一的方法就是“依乎天理”。
要想实现这种高级的养生,就必须有相应的工夫论,如何摆脱官能之知的局限,从而使“神”得以“行”,就是工夫的体现。而我们的眼光不能被这种神奇的手段吸引,而忘了其最终的目的,那就是合于天理的人生。
再来看“右师”的寓言,对于身体残缺的“右师”,人们惊讶于即便失去一足,也能够成为将军[⑩],因而发出感叹,这是天赋予的,还是人造成的。右师明确回答“知其天也,非人也。”也就是“天”让我“独”,而非人为所致。我们不知道这里的“天”指的是先天残障,还是右师将后天不幸导致残障之事平淡地归之于“天”,或是将身体残障却能成为右师的神奇之处归之于“天”。这里也没有出现身体残缺为何还能活跃于疆场的励志故事或者勤学苦练、最终掌握高超军事技能的工夫论。而是直接发表了右师关于“天”的理解,就是说“有与”(这里应该指代的是两足)的“人之貌”并不一定代表人的普遍面貌,失去一足的人同样是天之所生,因而和“有与”者是平等的。所以,这段话的关键词是“天”,如《人间世》所云“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在“右师”看来,“天”赋予了他超越残障的自信,因为不管肢体是否残缺,都是天之所生,不必因此自卑。
《人间世》里描述了身体残障的支离疏也能够享尽天年,“夫支离其形者,犹足以养其身,终其天年”。因此身体的残障并不会使“天”遭到破坏。养身主要靠的不是养形,而取决于内在的“德”是否保持圆满。《德充符》中被砍了一只脚的兀者王骀、申徒嘉、叔山无趾比正常人更懂得“不与物迁”“游心乎德之和”的道理。而哀骀它等“恶人”(丑陋的人)则是“才全”之人。所以“游心乎德之和”和“才全”都是德性圆满的标志,也是“天”未遭破坏的标志。“右师”的记载虽然很简短,但应该和《人间世》描绘的兀者同类。庄子还称“闉跂支离无脤”和“瓮盎大瘿”为“天食”之人,“天食”就是天养,所以“既受食于天,又恶用人”和《养生主》的“知其天也,非人也”恰好形成对应,那就是养生之主,在于按照“天”的方式去养,而不是按照人的方式。
依照上述的推理,再来看“泽雉”故事,就会觉得脉络非常通畅。首先,我觉得有必要调整一下句读,一般的标点是“泽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饮,不蕲畜乎樊中。神虽王,不善也。”而我则是“泽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饮。不蕲畜乎樊中,神虽王,不善也”。“十步一啄,百步一饮”指的是野鸡不受人为控制的自然状态。而不蕲即不祈求的内容是“畜乎樊中,神虽王,不善也”。[⑪]就是说野鸡不希望养在笼中,受人为控制,虽然不愁饮食,虽然精力旺盛,但却不“善”,这个“不善”,借助《人间世》的话,指的就是从此无法“受食于天”,违背天然。因此,这一段虽然没有出现“天”,但离不开“天”。
“老聃死”这段故事,讽刺了老聃弟子的行为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因为无论生还是死,都是受之于天。按照阴阳刑德的原理,如果生是“天之德”,那么死亡乃是“天之刑”,都是正常的、无法回避的,没有必要哭泣哀怨,所以要“安时而处顺”,不必因生而乐,因死而悲。而老聃弟子们却无法超然面对生死,乐生恶死,试图用哭泣、用哀怨去抵抗、去违背天的刑罚。所以在秦失看来,这仍然是被世俗礼法所拘,不能超然物外。所以这一段的关键词,毫无疑问就是“天”。
之于文章最后“薪尽火传”这段话,显然,“薪”代表的是有限的人生、有限的知,而“火”代表的是无穷、无尽、无限的生生洪流,而这不正是“天”的特征吗?总之,《养生主》各个部分都是以“天”为中心展开的,养生之主就是“天”,[⑫]只有“依乎天理”,只有“知天”,只有不受人为束缚,只有泰然接受“天之刑”,“安时而处顺”,才能获得无怨无悔的人生。因此从结构上看,《养生主》各段落是前后一贯,彼此呼应的。并无旁出的支脉,无关的论述。此处的“薪尽火传”也是天之道,自然之理。
二、没有生死观的养生观是不完整的
一般来说,战国时代的养生无论指的是养形,还是养神、养心、养性,都是以生存为范围的,即便在《庄子》其他篇目中也是如此。较之养形,以庄子后学为代表的道家更重养神,养形和养神常常被对立起来,[⑬]养形被认为是浅层的、外在的、不完整的、或者有意为之的养生。如《刻意》篇认为彭祖之类的人,不过是“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为寿而已矣,此道引之士,养形之人”,即刻意追求长生的人,依然采用的是人为的手段,违背了自然的原则。最高的境界是“养神”,《刻意》篇说“纯粹而不杂,静一而不变,惔而无为,动而以天行,此养神之道也。”能够让自己的心灵纯粹不杂、恬淡无欲,能够让自己的行动与天地合拍,那才达到了养神的境界。所以,养神才是养生的极致。《文子·下德》也以老子的口吻说:“治身,太上养神,其次养形,神清意平,百节皆宁,养生之本也,肥肌肤,充腹肠,供嗜欲,养生之末也。”
至于为什么要“养性”,这是因为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认为“性”(有时候称为“德”)是“天”所赋予的最为纯真、最为根本的东西[⑭],而人的一生,就是德性受到外物迷惑不断丧失的过程,如《天地》篇云:“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乱目,使目不明;二曰五声乱耳,使目不聪;三曰五臭薰鼻,困惾中颡;四曰五味浊口,使口厉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飞扬。此五者,皆生之害也。”《徐无鬼》云:“驰其形性,潜之万物,终身不反,悲夫!”而人类的历史尤其是进入文明以后的历史,就是德性被不断破坏,不断扭曲的历史。如《缮性》云:“逮德下衰,……德又下衰,……德又下衰,及唐虞始为天下,兴治化之流,浇淳散朴,离道以善,险德以行,然后去性而从于心。心与心识,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后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灭质,博溺心,然后民始惑乱,无以反其性情而复其初。”
庄子虽然没有直接使用“养性”这个词,但是使用了“反性”之类的表达,如《缮性》的“反其性情而复其初”。《缮性》还说“古之行身者,不以辨释知,不以知穷天下,不以知穷德,危然处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为哉!”即把回到初始的“性”作为修道的目标,这就预示着“性”是需要维护和保养的。后世道家则直接使用“养性”一词,如《文子·符言》以老子的口吻说:“治身养性者,节寝处,适饮食,和喜怒,便动静,内在己者得,而邪气无由入。饰其外,伤其内,扶其情者害其神,见其文者蔽其真,无须臾忘为贤者,必困其性,百步之中忘其为容者,必累其形,故羽翼美者伤其骸骨,枝叶茂者害其根荄,能两美者天下无之。”可见“养性”有两个方面的内涵,既有身体上“节寝处,适饮食”,也有精神上的“和喜怒,便动静”,才可以使“神”和“真”得到保护,所以“养性”既需要“养形”的工夫,也需要“养神”的工夫。
如果以养形、养神来看《养生主》,就会发现有显著的不同,首先此篇完全没有使用这些养生语境中常见的词汇,其次,此篇也并没有讨论相关的问题。虽然在文章的一开始提到了“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似乎养生局限在肉体生命的平安和长久上,但《养生主》并没有类似“节寝处,适饮食”,“和喜怒,便动静”,如何使肉体生命平安长久的集中论述。文惠君闻“庖丁之言”所悟得的“养生”,更像是如何处理好复杂的社会关系,从而使自己不受伤害。“右师”、“泽雉”的故事,则把合于天的生活方式视为养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养生主》中大谈对于死亡的态度,这确实令人意外。
在古人心目中,养生与送死是性质完全相反,可以形成鲜明对比的两件事。例如《孟子·离娄下》云:“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以当大事。”《礼记·礼运》说“昔者先王,……后圣有作,然后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为台榭、宫室、牖户,以炮以燔,以亨以炙,以为醴酪;治其麻丝,以为布帛,以养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可见“养生”“送死”是圣王要做的不同性质的两件大事。虽然《礼记·礼论》说:“礼者,谨于治生死者也。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终始俱善,人道毕矣。故君子敬始而慎终,终始如一,是君子之道、礼义之文也。”认为谨敬地妥善地处理生与死的问题,对于“君子之道、礼义之文”而言是一体之事,但也没有把“死”纳入到“生”的范畴,所以《养生主》的说法确实是独树一帜的。
但是,如前所示,《养生主》的关键词在于“天”。对于人而言,“生”与“死”间存在着难以愉悦的鸿沟。在种种二元对立,如大小、是非、美丑、善恶中,最难打破的就是生死的对立。对于“天”而言,“生”与“死”则不过是物化的两个节点而已,并没有本质的不同。或者说生死不过是一种同时成立的连环关系,可以兼具于一身,一边的生成预示着另一边的毁弃,那二元对立就不是纯粹的对立,而是双向的连环。正如《知北游》所言“死生有待邪,皆有所一体。”在庄子的气化论语境下,生与死实际上是一个整体,因此两者一定要同时提起,不能脱离一方而单独谈论另外一方。所以得道者要“游乎天地之一气”(《大宗师》)。
所以,可以有“养生”,未必要“送死”。因此,像秦失这样的得道之人,才会鄙视按照礼仪的规范做出形式化的“送死”活动。之所以将秦失的思想称为“悬解”,正因为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世俗的理解吧。所以《养生主》不是围绕养形、养神展开的有限的养生观,而是一种宏大的养生观,是一种包括如何面对死亡在内的宇宙论意义上的生命观。在庄子看来,没有生死观的养生观是不完整的,如果将个体的生命投入天地大化的洪流之中,那么“死”不过是无限之“生”的一个小小的停顿而已。如果我们把“指穷”理解为“死”,把“火传”理解为生生不息,《养生主》最后一段话就不是偶然的了。[⑮]
如果不限于《养生主》,我们可以发现,这种将生死合为一体的宇宙论意义上的生命观在《庄子》尤其内篇中是非常多见的。如《大宗师》云:“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⑯]死生之变犹如夜旦之常,极为正常。而且天地既用“生”来善待我,也用“死”来善待我,那为什么要有所区别呢?因此,没有必要专门从事“送死”的活动,把死看作是生的间歇,或许更为合适。
再来看《大宗师》以下这段话:
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者,至矣。知天之所为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养其知之所不知,终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虽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后当,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讵知吾所谓天之非人乎?所谓人之非天乎?且有真人,而后有真知。
这是把参透天人合一、生死之辩当作真正的“知”,当做是成为“真人”的标准,这不仅对于我们理解《养生主》“老聃死”一段有帮助,而且对于理解《养生主》“生也有涯”“知也无涯”的命题有帮助,因为“知之所知”代表的是有涯,而“其知之所不知”代表的是无涯,实际上也就是“天”。当用“知之所知”去养“其知之所不知”时,真人就出现了,“真知”也出现了,“终其天年而不中道夭”不就是《养生主》的“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吗?但只有“真人”凭借“真知”才能实现。《大宗师》这段话再次帮助我们理解了“养生主”之意,那就是要用有涯去养无涯,以“知之所知”去养“真知”,从而最终与天会合。
《大宗师》还描述了“真人”这一最高得道者对于生死的态度,“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其出不欣,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来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终;受而喜之,忘而复之。是之谓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这不就是秦失所说的“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吗?
《大宗师》中子祀、子舆、子犁、子来四人对谈的那段话中有:“孰能以无为首,以生为脊,以死为尻,孰知生死存亡之一体者,吾与之友矣。”秦失就是类似子祀、子舆、子犁、子来这样的得道者,在他们眼中“生死存亡”是一体的,类似于女偊所说的“能入于不死不生”。所以秦失会鄙视那些在生死面前患得患失的老聃弟子们,不愿与他们为友。既然“以生为脊,以死为尻”,那么,把生死的问题放在一起讨论,而不割裂开来,在《养生主》看来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四人对谈中再次出现了“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古之所谓县解”这样的话,我们无法考证究竟谁在前谁在后,但是利用《大宗师》关于生死的认识去理解《养生主》中为什么会出现死亡的问题,看来是最好的材料了。
三、如何活着:《山木》是《养生主》的最佳参照
综上所述,《养生主》中的“生”表面上看,是为了追求“保身”、“全生”、“养亲”、“尽年”,似乎只是为了肉体生命的保全和持久。但是,首先这个“生”并不排斥“死”,只有妥善处理“死”才能实现真正的“生”;其次,“养生”必须面对如何活着的问题,活着不仅仅是生命的延续,很大程度上也是如何妥善地安置社会人生、政治人生的问题。因此,养生既关乎宇宙论意义上的生死连续,又关乎现实社会中身体与精神如何安顿的问题。
社会人生、政治人生的问题,似乎并没有在《养生主》中全面展开,以至于我们在解读《养生主》时,更容易把养生视为一种技术,较多地使用外篇《达生》中承蜩老者、操舟者、善游者、削木者等事例,来阐述“技进乎道”时,对于事物认识的变化过程,“用志不分,乃凝于神”的重要性,以此来说明庖丁解牛为何会有“所见无非全牛”,到“未尝见全牛”,再到“更无牛”的三阶段,以及从“官止”到“神行”的必然性。如前文所示,这样的解读,容易把《养生主》的思想旨趣狭隘化,变成一种单纯的养生工夫论而已。
然而,我们认为,《养生主》作为一种宏大的生命观,说的是如何将生命融汇于大化流行之中,这种生命观既有其超越性的一面,也有现实性的一面。“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就清晰地点出了与世俗价值观之间不可避免的联系。“右师”“泽雉”“老聃死”三个故事都有其现实性的层面。“庖丁解牛”看上去不涉现实,但其实是个巧妙的比喻,说的是人如何才能行走于复杂的人间而全生,这一点已经是学界共识。[⑰]现实性的一面很难通过《达生》形成参照,因为《达生》弃世的味道很浓[⑱],而大谈如何处理现实人生的外篇《山木》却是一面很好的镜子,可以用来映照《养生主》的意趣。
我们首先来看那个“材与不材”的故事,大树因为“无所可用”亦即“不材”而免遭砍伐,得享天年。鹅因为“不能鸣”亦即“不材”而遭杀戮,不能终其天年。这个故事形象地比喻出人世间生存的艰难,几乎处处碰壁,很难有标准的人生答案,很难有畅通的人生之路。所以,庄子说他只能处于“材与不材”之间,即只能小心翼翼地游走于人生的夹缝之间,一不小心就会遇到阻碍,受到伤害。“材与不材”不正是“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的写照吗?即从事世俗所谓“善”之事时不要招致名声之累,从事世俗所谓“恶”之事时不要引发受刑之厄,最好处于中道,“材与不材”正是中道的象征。这当然不是说庄子赞同为恶,重点在于说明了“无近名”、“无近刑”的重要性,以免给自己的生命带来戕害。因为“为善”“为恶”作为两种极端人生路线,都有可能给人生带来灾难。
我们在阅读“庖丁解牛”的故事时,都会感叹庖丁游刃有余的精巧手段,然而庖丁即便十九年来刀未卷刃,仍然“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就是说即便有熟练的手法,在骨节聚集交错的地方,仍然不敢大意,必须目光专注、动作迟缓轻微。可见“庖丁解牛”并非随着工夫的深厚,而越来越轻松自如,随心所欲,其实是像《山木》所说的那样,“未免乎累”。因此,文惠君了悟之养生,未必只是“缘督以为经”的高超技能,很可能也包括了对于人生“未免乎累”的理解,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握养生的复杂性。
《山木》在其他的地方也描述过这种“未免乎累”的人生。如魏王问庄子“何先生之惫邪?”潜台词就是,像你这样的人应该活得很潇洒,为什么也会疲惫呢?庄子以猿猴为喻,说他们在山林间可以自由自在,称王称霸,神箭手也对他们无可奈何。但是到了低矮的灌木丛中,却只能“危行侧视,振动悼栗”,就像虎落平阳一样,必须小心翼翼,左顾右盼,恐惧战栗,即便有很好的身手也无法充分施展。这和《养生主》的“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是非常相似的。
所以我们读《养生主》,不能认为庖丁已经解决了所有的问题,为养生提供了所有的答案,其实庖丁的“累”也未免不是一种养生的启示。《山木》在感叹“未免乎累”之后,便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境界,那就是“乘道德而浮游”的境界,“无誉无訾,一龙一蛇,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一上一下,以和为量,浮游乎万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则胡可得而累邪!”这种与物迁移,悠游自得的状态,完全不受外物的拘束,也完全没有“累”的感受。要达到这一境界,只能“浮游乎万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即与道同体,从而无待逍遥。《山木》在市南宜僚的故事中,也提到这一点,那就是“人能虚己以游世,其孰能害之!”
《养生主》并没有提到“道德”“万物之祖”“物物”“不物于物”这些与“道”相关的概念,其关键词是“天”,但如前所言,“天”是可以作为万物发生之源、存在之理和必然归宿的,因此具有与“道”同等的高度。“庖丁解牛”之后的“右师”“老聃”故事都指向了“天”的重要性,“泽雉”故事则在反对人为的同时,突出了天然的重要性。因此,《养生主》也有一个逐渐上升到“天”,在天人关系中了悟养生之道的过程,其最终的归属就是安时处顺,天人合一。
《山木》同样谈到了天人关系,在“孔子穷于陈蔡”那段故事中,孔子向颜回提出了四个命题,即“无受天损易,无受人益难。无始而非卒也,人与天一也。”
所谓“无受天损易”,说的是“饥溺寒暑,穷桎不行,天地之行也,运物之泄也,言与之偕逝之谓也。”即饥渴寒暑、穷困潦倒这些人生的困境,正是天地万物运行变化的表现,既然不可逃,就恬然受之,与之偕行,不生怨责。这样虽然遭遇困境也不会感觉受损。因为这是比较容易做到的,所以说“无受天损易”。但处于顺境时,能够拒绝不属于自己的利禄就难了,所以这叫做“无受人益难”。这两个命题都说的是人生困境。这些困境既有来自于天的,也有来自于人的。
“无始而非卒”说的是“化其万物而不知其禅之者,焉知其所终?焉知其所始?”在事物变化的连续过程中,既不知道谁是替代者也不知道谁是被替代者,既不知道事物的开始也不知道事物的结束。这也应该说的是包括人在内世间万物之变化的流动性和复杂性,使人无所适从,难以把握。所以只能“正而待之”,即顺应事物的变化而不与之相悖逆。
最后孔子总结道:“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圣人晏然体逝而终矣。”这就是“天与人一”的命题。这个命题可以看作是对上述三个问题的全面回答。孔子认为“天”固然是“天”,而“人”也在“天”的范畴之内,人不可能超越天、控制天,这是一种不可改变的“性”。所以人的最佳处身方式就是顺遂天地的大化,而与之偕行,直到生命的终结。这样的回答和《养生主》中“右师”对于自己的遭遇淡然处之而归之于天的回答——“知其天也,非人也”的表达几乎如出一辙,而“圣人晏然体逝而终”则与秦失“安时而处顺”的精神几乎如出一辙。
余论
总之,《养生主》虽然谈养生,主要不是一种关于关于养生的工夫论。其关键词是“天”,养生之主也就是“天”,整篇文章紧紧围绕“天”字展开,论述了一种宏大的生命观,这种生命观的超越性足以涵盖生死观,这种生命观的现实性足以回答人如何在现世合理地活下去。继续《养生主》所未竟的话题,内篇的《德充符》《大宗师》和外篇的《山木》在生死观和天人观上有进一步的开拓,彼此照应的关系是比较明显的。
但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需要回答,即如何界定《养生主》中的“天”?换言之,如何确定《养生主》中“天”与“人”的关系?如此强调“天”的地位和作用,是否可以说《养生主》中“人”完全笼罩于“天”的阴影之下,没有自己的能动性可言。
毋庸置疑,不仅《养生主》,即便整个《庄子》中,“天”都不是类似宗教世界中神格的存在,相对于“人”居于绝对的主宰地位,人也不是匍匐于“天”的权威之下的卑微的没有意义的存在。如“庖丁解牛”所示,“人”甚至可以通过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使得官止神行,遵循牛天然的生理构造,在解牛工艺中达致人与天的合一,因此“人”和“天”并不是割裂的关系。
然而,在《养生主》大部分语境中,“人”与“天”的二分还是很明显的,“人”指向狭隘的、有限的、不合理的人为,而“天”则既是人个体自然生命的来源与归属,也是社会生命行为的准则、价值的保障、和命运遭际的合理性安顿,所以无论本始状态的生命、社会关系中的生命,还是宇宙大化中的生命,都最终全部归属于天。因此在“人”与“天”之间,庄子当然首先选择“天”。荀子正是感受到了这一点,才对庄子做了“蔽于天而不知人”的评价吧。
在《庄子》各种不可思议的技艺描述中,人与天的合一都是其重要特征,而这恰恰是修道工夫中必经的途径、追求的境界。这也是《庄子》喜欢大量记载类似“庖丁解牛”故事的原因吧。然而,在《庄子》的天人关系论述中,对现实中天人相分的批判,对理想中天人相合的追求还是最为常见的,形成其一贯的基调,《养生主》的天人关系也以此基调为主,站在荀子的立场,这种基调确实会给人“蔽于天而不知人”的错觉。
(作者曹峰,本文原载于《船山学刊》2024年第5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