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庆丨戴蒙德新作《剧变》:从国家地缘政治看危机应对策略
日期:2020-04-16具有生理学家、史学家和科普作者等多重身份,美国资深学者贾雷德·戴蒙德凭借《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在世界范围内闻名遐迩。《枪炮、病菌与钢铁》具备自然科学的外观,试图基于自然环境的决定性因素,和技术文明对自然的反作用历程,概括作为“人类史”的文明史轨迹。显然,戴蒙德延续的是十八世纪末以来西方启蒙主义人类学的基本思路:根据置身自然存在之链中的“人类”生理属性,理解“人性”在社会和文化层面的秩序化、观念化的整个机制。
在启蒙哲学的大环境下,从孟德斯鸠到康德的历史哲学都会相信,人类的自然实存状况,是文明秩序获得稳固奠基的首要参考系统。戴蒙德也正是基于这一大前提,试图跳出当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设立知识壁垒、互不往来的困局,重建自然状态-文明秩序的历史叙事线索。因此,我们也就能够理解他的新书《剧变》(Upheaval: Turning Points for Nations in Crisis)的内在思路——通过审视各个民族作为生存实体的现实选择,思考并理解其社会和民族国家机制在回应危机时的功过是非。
在中国面临各种历史危机的当下,《剧变》能否给予我们思想上的启发?这就要求我们首先简单回顾一些曾经作为风险回应机制而出现的重要政治思想。譬如,《剧变》在一开头就提示我们注意到西方直面时代危机的最初传统——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史学写作:
本书采用叙述性写作风格,这是历史学家传统的写作方式,最早可追溯至2400多年前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将历史发展为一门学科时。(页xvi)
古希腊史学的叙述性写作,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风格。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期待戴蒙德给我们带来一种古典式的历史叙述和分析呢?至少戴蒙德有意识地没有采用现代科学研究的常规定量方法和档案史料研究法展开写作,也没有试图把野心扩张到“全球”,而是有选择地以7个国家在具体时间段内的情况为案例。和古希腊史家有点类似的是,戴蒙德选择这些国家作为例证:
是因为我或多或少有在这些国家生活的亲身经历,或是有朋友在这些国家,而且我熟悉其中6个国家的语言,探讨这些国家对我而言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页xviii)
戴蒙德诚实地绕开了自诩“全面”“系统”和“科学”的现代“全球史”逻辑,更多地将史学写作集中在自己作为一个有限观察者凭借常态视角就能清楚呈现的现实经验层面。当我们在阅读时,可以明显感受到戴蒙德对本己经验的重视,也可以体会到这种视角相比起司空见惯的社会科学或档案史学所具备的亲和力。为了强调这种亲和力,戴蒙德还在开篇特地提出了他乍看之下显得略不着边际的方法论:在面对巨大危机时,个人的反应和国家的反应之间,或许具有某种可类比性,这是因为:
……一国的文化为该国民众所共享,而且一国的决策最终取决于该国民众的观点,尤其取决于其领导者的观点,而其领导者也深受该国文化影响。(页23)
对于现代民族国家来说,民众的“公意”的确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领袖的法理地位则是对这种公意的象征和执行。因此,如果国民具有某种普遍的“国民性”,并依据这种国民性而集体行动,那么不妨将国家想象为一个大写的、有机的“个人”。据此,戴蒙德相信,我们或许可以凭借个人的危机体验来理解国家的危机应对策略。

《剧变:人类社会与国家危机的转折点》
(美)贾雷德·戴蒙德 著
曾楚媛 译
中信出版社
2020年4月
受地缘政治影响的国家有哪些求生经验
依据其所总结的“影响个人危机结果的因素”,戴蒙德列出了11个“影响国家 危机结果的因素”:
对国家陷入危机的举国共识
愿意承担责任
划清界限,明确需要解决的国家问题
从他国获得物质和资金方面的帮助
借鉴他国应对危机的经验
国家认同
诚实的国家自我评估
应对过往国家危机的经验
应对国家失败的耐心
特定情况下国家的灵活性
国家核心价值观
不受地缘政治约束。(页23)
在其中,和“个人因素”最不一样的是第一条。“个人因素”第一条是“直面身处危机的现实”。常识告诉我们,对于个人来说,要认识到危机来临的现实,往往需要提升的是个人的认识能力和敏感度。但对于国家来说,要达成对危机的“举国共识”,这并非那么容易。
比如说,在今年初的新冠肺炎疫情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若非专业医学人士提供权威预警,一般人很难认识到这种病毒的破坏性。对于个别民众拒不依循防疫措施的情况,国家只能采取强制手段。在举国危机的问题方面“达成共识”,在这个意义上是一种十分理想的状态,其难度远远大于让某一个体认识到自身所处的巨大危机。因为国家的危机往往在更为巨大的时空幅度当中来临,要准确厘定这种危机,需要专业技术和权威机构的引导,而多数民众往往无法凭借自己的有限理性,给出彻底现实、有效且符合公共利益的判断。
一旦意识到“个人因素”和“国家因素”在最根本的层面难以达成一致,戴蒙德的理论体系也就会出现显著的令人疑惑之处。让我们再来思考最后一项因素:戴蒙德对“个人因素”的表述是“不受约束”,而在“国家因素”层面,他强调了“不受地缘政治约束”的特殊性。许多有条件的普通人当然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他们可以凭借自己的判断、行动而决定和什么人来往,并有效保持独立。但国家间的地缘政治则并不是这么回事:自然环境和历史因缘决定了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邻国、盟友和敌人。同时,地缘政治带来的危机在剧烈程度和频繁度方面,也会远远超出普通个人的想象。戴蒙德的第一个国家例证——芬兰——便可说明这一点。
在戴蒙德的叙述中,大量关于风土民情和语言文化的叙述未能掩盖芬兰在地缘政治上的天然不足:就地理位置而言,芬兰夹在俄罗斯和德意志两大现代强权民族之间,进而,其国际政治选择极为有限,这一点在戴蒙德所叙述的二战前后的芬兰外交简史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在面临苏联的进犯危机时,芬兰无法从其邻近但缺乏友好往来的瑞典等国获得有效援助,只能寄希望于英法,而英法则抱有控制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矿产资源和海域的真实目的。虽然凭借民族主义的动员,芬兰将苏联拖到了和德国关系破裂的时机,并被迫和纳粹德国联盟。尽管如此,芬兰依然遭遇两个大国在各方面的继续剥削,甚至在战后面临苏联的赔款要求,并继续在东方和西方的夹缝中挣扎求生。戴蒙德在此讲述了他在芬兰时的一次重要的经验:
当时,我问在芬兰的几位房东,芬兰为什么要实行那些政策,为什么要进口那些质量不那么好的莫斯科人牌汽车,为什么那么害怕与苏联发生冲突。我告诉他们,倘若芬兰真的与苏联发生冲突,美国肯定会帮助芬兰的。现在回想起来,可能再没有别的话会比我所说的这些更让一个芬兰人感到残忍、无知以及不得体的了。在芬兰的国家记忆里,充斥着这么一种难以言说的苦痛:在1939年苏芬战争爆发之际,无论是美国、瑞典、德国、英国还是法国,都没有对芬兰伸出援手。这段历史告诫着芬兰人,芬兰的存亡和独立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页61)
这段话清楚地表明了“小国”的地缘政治生存现实。在相邻大国的压制下,小国没有任何绝对“独立”自处的空间,而只能尽可能用政治和外交手段争取和平和发展的余地。同时,渴望通过国际的“友谊”来化解这一根深蒂固的矛盾的思路也是不切实际的。即便无法“独立”,但最终能够依靠的,只能是“自己”。因此,戴蒙德让我们注意到:
……芬兰人深知,际遇无常,因此芬兰要求该国男性义务服兵役,并欢迎女性志愿参军。芬兰人在服兵役时要接受最长一年的严格的军事训练,因为芬兰的期望是,每一个芬兰人都具备上战场的能力……芬兰的预备军人数占该国总人口的15%,倘若这一比例放在美国,那就相当于拥有一支5000万人的预备军。(页62)
戴蒙德对芬兰面对危机的总体态度进行了系统的总结:
芬兰人唯有在生死存亡之刻,才开始对身处危机的状态有了“全民共识”。在这漫长的危机历程里,芬兰人学会了“现实主义”,亦即戴蒙德引用《纽约时报》所表达的“芬兰化”:“在一种可悲的状态下,一个弱小的国家屈服于强大的邻国,对自己的主权自由做出可耻的、令人尴尬的让步。”(页61)
这是小国的无奈,也是其化解危机的唯一办法。
芬兰就像是一个天生弱小的人类个体,不断寻求着生存的空间。不同的是,一般的个体人类可以通过迁移和自我强化的方式摆脱他者的控制——毕竟,人和人之间的差距,不可能像国和国之间的差距那么大;但国家受限于先天的地理、人口、资源和历史条件,其实存的力量必然不可能在短期内获得长足的提升。进而,谋求地缘政治上的“不受约束”,对于芬兰来说是不切实际的。
在戴蒙德看来,日本则和芬兰不一样,岛国的地理环境使得其长期免于受欧亚大陆强大力量的彻底支配,尽管遭遇过佩里叩关这类挑战,但日本可以通过漫长的国内政治经济改革,打造统一意识形态,从容不迫地推进自身实力的增长,从而化解危机。问题在于,在初步实现“脱亚入欧”并在20世纪初成为世界级强国后,日本对外界、尤其是对美国实力不够了解,使得其国际事务决策出现巨大失误,过于乐观地把国家推向战争主义的旋涡,这实则与其维新变法的先辈在思维上背道而驰:
明治时代的日本领导者成长于一个内外交困的弱小的日本,内有纷争冲突,外有潜在的西方强敌。而在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领导者眼中,战争是成功的代名词,他们沉醉在日战争的胜利中。(页96)
尽管如戴蒙德所说,日本在地缘政治局势方面似乎处于得天独厚的优势,并在其他的“国家因素”方面(如善于学习他人经验和打造举国认同等方面)做得十分到位,但最终日本仍然主动陷入危机不能自拔。戴蒙德没有很好地解释这一点,或许是他对于“地缘优势”的理解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相比起孤悬于欧亚大陆之外的美国,日本的地缘优势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同时,美国国土广袤、资源丰富,并且远在日本之前已经对太平洋地区进行势力扩张,甚至可以等同于日本在太平洋上的巨大“邻国”。当日本试图在地缘上崛起成为区域霸主时,美国必然成为其不可回避的对手,日本也会将美国的存在本身视为解决生存发展危机的首要障碍。戴蒙德对此一笔带过,似乎美国远不如苏联那样令周边邻国畏惧。
因此,虽然看似没有陷入芬兰那样令人窒息的地缘宿命,但日本东和美国、西和亚洲大陆传统大国之间的必然性碰撞的激烈程度和带来的危险系数,未尝会低于芬兰。在和个人的日常生活非常相似的和平年代,日本能够凭借其孤悬海外同时又积极变革的优势化解一些常态性危机,但这并不意味着作为一个自然条件天然受限的国家单位,日本可以永远化险为夷。身为自然科学家,在描述国家风险时,戴蒙德却甚少分析日本遭遇过的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或许是他并不具备对这种真正危机的现实体验,自然也不会去回溯关东大地震造成的精神创伤和日本军国主义之间在民族情感结构方面的内在关联。
当然,正如没有哪一个具体的人能够免于天降横祸,也不会有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能够免于无妄之灾。和日本一样位于地震带的智利,也受到了戴蒙德的注意。不过,戴蒙德更多提醒我们,同样作为美洲国家,同样有着民主政治的传统,智利却与美国分道扬镳,“结出了一颗专制的果实”(页107)。智利狭长的国土、特殊的历史和国民种族成分,使得其国民能够在理论上团结一致,但人为的政党斗争,则使得国家乏于处理分裂难题。尤其在冷战时期,为了遏制左翼在拉丁美洲的扩张,美国积极扶持智利的右翼势力,与阿连德的激进政策形成对抗局面。戴蒙德则引用“几个智利朋友”的观点,认为阿连德被过往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并在个别激进派的怂恿下“脱离现实”。戴蒙德甚少讨论美国中情局颠覆阿连德政权并推皮诺切特上台的具体手段,或许他认为这种外来的干预只不过是“苍蝇不叮无缝蛋”的自然表现。
从智利的国家利益角度来说,戴蒙德虽然指责皮诺切特的残暴专横,但也承认其经济政策的片面的意义。但最终,戴蒙德和其“智利朋友”一样,致力于思考这样的根本性问题:智利处理危机时难以落实平衡稳定手段、而不得不走向或激进或极权等极端选择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具有全球视野的戴蒙德这时给出了一段地缘政治分析,值得我们注意:
智利还展现出能自由行事的优势和受到约束的劣势……智利与毗邻的拉丁美洲国家之间有高山和沙漠为阻隔,这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阿连德政府或皮诺切特政府的担忧……不过,阿连德政府的行事自由受到远方的美国制约,历届智利政府的行事自由还受到本国铜矿产业参与全球市场程度的约束,而全球市场状况则是智利无法控制的。(页136)
智利无法凭借自身内部的结构性调整化解危机。这种尴尬的根本缘由,或许和日本一样,要到外部的地缘环境当中去找寻。智利像日本而不像芬兰,表面上没有威胁性极大的邻国干预其政事民情。但在一个世界市场逐渐形成、且由超级大国主宰美洲-太平洋地区政经大势的时代,智利注定会和当初的日本一样,选择主动创造“剧变”以获取生存空间,而非顺应外来的一切约束。当然,戴蒙德更多地关注智利“剧变”的暴力面貌、强权领袖和所谓“犯罪行为”等因素,显然是没有意识到,就整个人类历史来说,小国、弱国在“霸凌”的秩序之下选择“以暴制暴”的反弹行动,并不乏见。芬兰被迫加入纳粹德国阵营、日本对美国的挑衅和智利的独裁化,均体现着同样的民族生存困境。戴蒙德未能留意到这些国家先天的不足,却试图从它们那里找到让美国不至于陷入极端状态的历史教训。
接下来,戴蒙德试图以印尼为例,反思这种极端暴力行动(大屠杀)。作为一个长期被西方人殖民、且宗教和文化结构极端复杂的多民族国家,印尼和前述的几个可以有效达成国民认同一致的国家有着巨大的差异。印尼的体量更大,地缘关系更加复杂,其政治整合的实现,也更加困难。和皮诺切特一样,引领大屠杀的苏哈托同样仰赖美国在各方面的“友好帮助”。戴蒙德提醒我们,极端暴力的意识形态形成过程,和其依赖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步调几乎一致:
就像是智利的案例中皮诺切特将军找到了“芝加哥男孩”,苏哈托的“伯克利黑帮”通过平衡预算,削减补贴,以市场为导向,减轻印度尼西亚的国家债务和降低通胀水平来推动经济改革。(页162)
苏哈托政权的崩溃和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息息相关,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历史的“巧合”。尽管对大屠杀及其背后的极权基调表示出明显的反感,戴蒙德还是会暗示,正是在这种极端暴力行动中,印尼人更有效地践行了其民族的整合工作,但同时也失去了其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扩张契机。但无论如何,从生存空间的拓张角度来说,作为后发国家的印尼在20世纪的当务之急,当然是用一切手段夯实自身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方面的根基。
如果说,戴蒙德对印尼和智利主动制造危机的极端措施(极权政治、大屠杀)持总体上的批判态度(但并不杜绝对其内在逻辑的细致理解),那么,对于同样属于西方文明的战后德国,戴蒙德更多地表达了同情,但还是会指出,这个国家虽然“权威主义色彩已经大大淡化”,但“仍旧处于权威型社会”(页194)。同时,和芬兰、日本、智利与印尼都不同,德国遭遇的危机并非“突发事件”,而是在长期的阵痛式冲击中积累而成的结构性灾难。戴蒙德再度运用地缘政治因素解释德国的危机:德国地处欧洲中部的“四战之地”,俄国、英国、法国等强国环伺四周,使得其不得不在军事和政治上以强势的姿态夺取生存空间,但与此相伴的则是遭遇强敌更为严酷的压制和掠夺。进而,德国不可能成为地缘政治上的主导者,而只能陷入“自我怜悯和受害者心态”(页202)。对此,戴蒙德认为,如果不能出现能够凭借现实主义心态从事灵活外交活动的领导者,如果国家无法在选择性变革中延续强烈的集体认同,那么这样的德国也就无法走出其结构性危机。
到此为止,我们留意到,戴蒙德所分析的,基本上都是地缘位置较为恶劣且面临诸多历史遗留问题的国家。接下来出现的案例澳大利亚,则显得像个例外。用戴蒙德自己的话说,澳大利亚的危机问题是“关乎国家认同和核心价值观”的——这个国家远在亚太地区,却由英国奠定其政治文化结构。澳大利亚的地缘环境可谓得天独厚(戴蒙德甚至称其“不受地缘政治约束”),但其独立自主却依然需要和宗主国讨价还价。澳大利亚的发展,依然无法脱离世界级别的大国博弈。一旦认识到全球化时代的地缘格局已经远远不同于过去,那么我们也不能认为澳大利亚可以就此成为“海外乐土”,否则,也就无法理解,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为何非得由澳大利亚组成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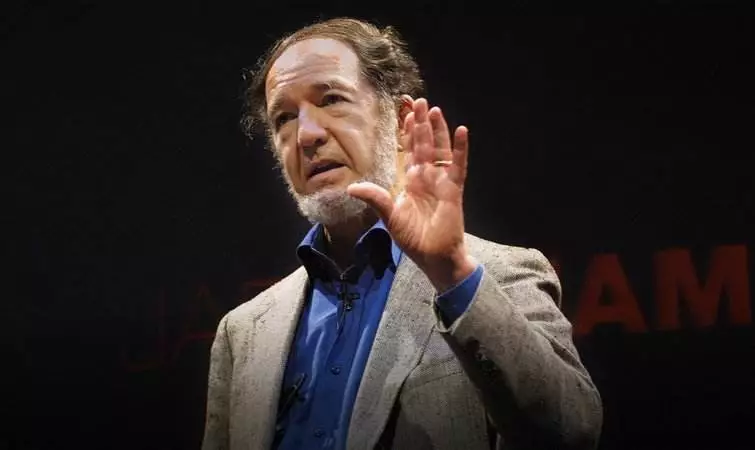
▲贾雷德·戴蒙德(JaredDiamond)
是什么造就了美国的危机
戴蒙德上述的几个国家危机案例分析总体上让我们学到了以下几点:首先,对地缘政治局势的分析,在理解国家危机之根源方面,或许仍然具有主导意义。尽管许多国家看似具有地缘优势,但究其危机出现的时代背景和经济动因而言,其背后的决定性因素,都是地缘政治上的掣肘博弈。然后,尽管戴蒙德选择的国家看似具有随机性,但我们可以总结出其中的共同点:
1、这些国家都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大国或强国,或是国土和资源有限,或是历史、文化和民族凝聚力等方面有先天的短板;
2、这些国家事实上被其他巨大力量左右甚至决定着,但却看似具有显著的独立意志,显得像是“自由”的个体,或是有独立的强烈意愿。
3、这些国家所遭遇的危机,大多和美国自二战以来试图建立的理想全球秩序有关,甚至可以说,它们努力化解自身危机的尝试,总是和一股辐射面更广的政治节奏彼此应和——即美国调整并重构世界秩序的节奏。
作为一位擅长从风险危机的整体结构角度描述问题的专业史家,戴蒙德谋划的这一问题线索,显然不能脱离作为20世纪第一大国的美国。因此,在接下来的篇章中,我们果然读到了他对美国的讨论。
戴蒙德会怎么讨论美国人所面临的危机及其回应机制呢?不出意外地,他首先提到的关键点,就是中国崛起。中国在经济、科技和政治影响力等方面的巨大潜能,令他和其他美国人相信:“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当真是美国有史以来最令人焦虑的10年。”(页280)和中国相比,美国在国力、地缘等方面的优势是显著的。但随着“本应秉持民主制度的美国政府正因日渐偏离真正的民主而失去了部分潜在优势”,美国人开始羡慕“那些在制定和执行好的政策方面富有成效的国家”(页287)。戴蒙德试图维护美国的民主传统,让美国不至于走日本、德国乃至于智利的老路,选择用极端暴力的手段来面对危机。与此同时,美国还应当维持其社会经济的较高流动性,以此来唤起民众的潜能,而“移民”,则是保持这种流动性、创新性优势的重要因素。
戴蒙德坚信,由于对民主的信念缺失,美国人丧失了“政治妥协”的能力,只会在过度激进的示威表态和程序性阻挠议事等剧目的反复上演中虚耗光阴和资源。在日趋贫乏而机心算尽的选举政治局面中,美国政治正在朝向极化方面发展。虽然媒介技术狂飙突进,美国人获得了更多的选择空间,但这反而加剧了他们“根据自己先入为主的观点来选择接收信息的来源”,进而:
这样的结果是:我把自己封锁在一个为自己量身定制的政治壁龛中,我只承认自己认同的那一套“事实”,我继续为我一直支持的党派投票,我不了解对方党派的支持者为什么会做出跟我不同的选择,当然,我也不希望自己投票选出的代表和那些跟我政见不同的代表达成妥协。(页300)
显然,戴蒙德担忧,互联网上的部落化、趋同化会导致现实政治中的极化趋势。这种趋势甚至还会渗透到日常行为乃至于科研领域中:
我如今不断受到来自和我意见相左的科学家的起诉或威胁,而且他们还会对我使用语言暴力。邀请我去讲课的主办方曾经不得不雇用保安人员,以免我受到那些极端反对者的攻击。在针对我的一本书所发表的书评中,一名学者以“闭嘴吧!”这样的字句作为结语。美国的学术界和我们的政治家、我们的选民、我们的电梯乘客、我们的汽车驾驶人、我们的行人一样,都反映出了美国人的整体生活状况。(页302)
与这种群体极化的趋势相应,传统的共同体纽带日益薄弱,公民美德随之丧失,在个人主义盛行的美国,彼此出于极端政治立场而敌对仇视的僵化局面,会随之成为主流。戴蒙德甚至担心,这样下去,美国可能会和智利一样,陷入更为显著的政治暴力旋涡当中。作为一位年长的传统知识分子,戴蒙德严肃地提醒美国人,必须直面由政治极化所指涉的全面社会矛盾,如贫富差距扩大、公共教育投入减少等。根据戴蒙德自己的理论框架,美国占有地缘、文化认同、灵活性等方面具有先天优势,但却甚少学习其他国家,并最终在“举国共识”这个问题上,遭遇根本困境。按照戴蒙德自己的类比逻辑,国家在民众共识上一筹莫展,等同于一个个人无法具有起码的生存意识,无法“直面身处危机的现实”:
目前美国人对于自己的国家是否陷入危机缺乏共识;美国频频将自己的问题归咎于他人,不肯承担自己的责任;太多有权有势的美国人只想保护自己,不愿出力改善自己的国家;还有我们不愿意借鉴其他国家解决类似问题的模式。(页333)
到此,我们才能全面理解戴蒙德此书在何种意义上具有严肃的史学品质:为了有效说服自己的民族和国家直面危机并探寻务实的解决之道,戴蒙德以其他国家为依据,最终落实到对美国的褒贬上。美国需要学习其他国家的治乱安危之道,这不仅是一个美国本国治理层面的问题,还是世界整体和平发展格局能否有效延续的问题。在全球化的大语境之下,对核武器、气候变暖、能源共享和我们今天最为感同身受的防治疫病等话题的回应,都要求我们在“被迫进入全然不熟悉的领域”之时,重返“剧变”来临的前夕,借鉴各国的经验进行思考。对此,戴蒙德提出,形成“区域性协定”乃至于形成“全球共识”,是一条理论上的必经之路。问题在于,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尚且难以实现“举国共识”。要让全世界骤然达成“全球共识”,又谈何容易?
在结语中,戴蒙德再度重申了“直面现实”的重要性。一个现代国家需要对自身有诚实的评估,也要努力学习他国的经验,发挥灵活性,懂得应时而变,还要塑造国家核心价值观——这些平平无奇的历史建议,被戴蒙德不厌其烦地重述。但最为关键的一点建议“不受地缘政治约束”,若要落实,则显得格外艰难。事实上,地缘政治冲突,往往是国家危机的主要原因。无论地理处境恶劣的芬兰和德国,还是相对优越的美国和澳大利亚,在一个洲际导弹和“天电网”当道的时代,也无法像两千多年前的希腊和波斯那样,回避漫长而残酷的文明碰撞和空间博弈。在这个层面,“现实主义”的眼光也就并未过时。
戴蒙德的这本书,对我们的启示也更多地体现为两方面。首先,在国家认同和自我评估方面,中国应当“以美为鉴”,认识到政治极化、阶层分化和政治重心不明确的危险性。在这个层面,我们或许可以把戴蒙德提出的“认识自己”“直面现实”等化解“个人危机”的因素,理解为政治家个人必须具备的修养。正如戴蒙德所言,领导者有时的确能够产生决定性影响(页400)。基于有现实主义眼光的政治家、领导者的稳重谨慎行动,国家凝聚力和“公民共识”等议题,也将找到落实的抓手。
然后,在地缘政治方面,中国天然存在着长处和短板:中国绝不可能“芬兰化”,也不可能变成下一个日本或印尼,这是由我们辽阔的地缘纵深所决定的;然而,复杂的四邻关系和国际环境也构成中国崛起遭遇危机的潜在温床。相比起戴蒙德所说的那些“需要在危机的刺激下才会采取行动”(页396)的地缘政治被动者,中国应当更多地吸收历史的教训,用冷峻清醒的眼光观察世界格局,尤其是要“克服许多的惯性和阻力”。在面临“新冠肺炎”这类“突发性重大问题”时,我们虽然承受了前所未遇的危机,但也收获了在紧急关头整饬社会、改革体制且重构国家信念的宝贵经验。虽然历史的潮流在不断奔涌,但浪花升腾和消散的基本形态却不会有太多变化。熟悉了风浪的规律,就会明白,危机和剧变总是不离政道人心之理。而要揭示这种政道人心之理,我们不妨学习戴蒙德在全书结尾处提到的修昔底德,在占有更多论据的今天,依然保留最为现实的态度,看清这个实力导向的世界,并“践行诚实的自我评估”(页408)。


